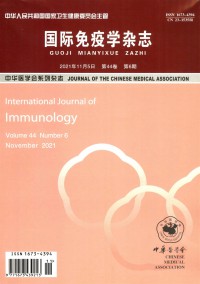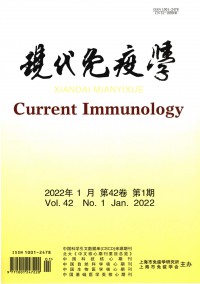免疫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免疫病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免疫病范文第1篇
【關鍵詞】 乙型肝炎;病毒;自身免疫
自身免疫病是指機體對自身抗原發生免疫反應而導致自身組織損害所引起的疾病。其病因尚未完全清楚,目前認為與遺傳、環境、代謝和感染等因素有關。近年關于病毒感染與自身免疫病發病研究較多,其中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與自身免疫病發病的相關性受到廣泛關注,較多研究表明HBV感染與自身免疫病發病關系密切[ 1,2],其機制可能是HBV通過分子模擬、Bystander effects(旁觀者效應)、抗原表位擴增、刺激非免疫細胞表達MHC分子等誘發產生自身抗體和激活自身反應性T淋巴細胞導致自身免疫病的發生。HBV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現就HBV與結節性多動脈炎、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等自身免疫病發病的關系做一綜述。
1 HBV與自身免疫病
HBV可以通過上述機制誘發自身免疫反應并導致相應的疾病,下面就分別闡述HBV與結節性多動脈炎、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和多發性硬化發病關系的研究。
1.1 HBV與結節性多動脈炎 結節性多動脈炎是一種主要侵害中、小動脈的壞死性動脈炎,病變呈節段性分布,可侵犯全身各血管。其臨床表現復雜多樣,可累及腎臟、肌肉、皮膚、神經、消化等多個系統。結節性多動脈炎病因未明,目前認為其發病機制與免疫復合物沉積密切相關。國內外關于結節性多動脈炎與HBV感染相關性的研究表明HBV抗原抗體復合物的沉積在該病發生和發展過程中均起到重要作用。Guillevin等[6]進行了一項包括115例乙肝相關性結節性多動脈炎的研究并回顧分析了結節性多動脈炎在法國的流行病學情況,結果顯示在1972—1989年之間的結節性多動脈炎患者約50%伴有HBV感染。此外, 該研究表明,由于輸血安全性提高以及乙肝疫苗預防接種導致乙肝感染率降低,同時結節性多動脈炎發病率也隨之下降,這說明HBV感染在結節性多動脈炎發生和疾病發展過程均起到重要作用。
治療上,乙肝相關性結節性多動脈炎在進行免疫抑制治療時主張與抗HBV的藥物聯合使用,否則容易在停藥后誘發HBV的復制加劇,甚至導致肝功能急劇惡化[7,8]。其機制可能為治療結節性多動脈炎的藥物抑制機體免疫系統(尤其是細胞免疫)從而抑制機體抗HBV的能力導致病毒復制活躍,在停藥后機體免疫功能恢復導致免疫相關性損傷。因此,在進行乙肝相關性結節性多動脈炎治療時應該考慮聯合使用抗病毒的藥物。
1.2 HBV與系統性紅斑狼瘡 系統性紅斑狼瘡是一種多系統、多臟器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臨床表現多樣,病變累及全身多個系統。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血清免疫學表現復雜,可以出現ANA、抗dsDNA、抗ENA、抗磷脂抗體等多種自身抗體。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因不明,可能與遺傳、環境、感染、性激素等多種因素相關。
關于乙肝與系統性紅斑狼瘡發病的關系,不同研究差異較大。一些較早的文獻報道表明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HBsAg攜帶率高[9,10]。而曹永獻等[11]用ELISA法測定131例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與582例健康體檢者HBV標記物發現SLE患者的HBsAg攜帶率為陰性,明顯低于體檢健康對照組(7.7%)。分析其原因可能為SLE患者體內IL-10水平較高,而IL-10可刺激機體產生抗HBV的抗體相關,其中HBsAb為中和抗體,能夠中和乙肝表面抗原,這可能是引起SLE患者HBsAg下降的原因。另外,仇寧等[12]通過SLE與其他皮膚病患者的血清HBsAg攜帶率測定結果為兩者差異無顯著性,該研究結果表明SLE發病與HBV感染無明顯關系。這些不同的研究結果出現如此大的差異可能與地域流行病學差異有關,也可能是由于不同遺傳背景或其他因素影響造成的。因此,關于HBV與系統性紅斑狼瘡發病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1.3 HBV與類風濕關節炎 類風濕關節炎是以對稱性、進行性及侵蝕性關節炎為主要臨床表現的系統性自身免疫病,除關節受累外,常可累及呼吸、消化、血管等多個系統。病變呈持續性、反復發作過程,如果未經早期及時治療常常會發展為關節畸形導致關節功能障礙。其發病機制至今尚未闡明,可能與遺傳易感性、環境和感染等因素有關。
類風濕因子(RF)是類風濕關節炎診斷和病情評估的一項重要指標,而諸多研究表明HBV感染患者血清中RF陽性率較高。周明歡等[13]通過對160例HBV感染者血清自身抗體檢測,該研究結果顯示在HBV感染者血清中RF陽性36例(22.5%),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表明HBV可能在類風濕關節炎發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Lee SI等[14]對176例患者血清IgA RF、IgG RF、IgM RF檢測結果陽性率分別為29.5%、21%和18.8%,同樣支持HBV感染者RF陽性率增加的結論。以上兩項實驗都說明HBV感染在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病中可能為誘發因素。
1.4 HBV與多發性硬化 多發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一種常見的中樞神經系統脫髓鞘性自身免疫病,其特點為大腦與脊髓內出現播散的脫髓鞘性斑塊,臨床表現為多樣性神經系統功能缺失,病程進展緩慢,常緩解與復發交替進行。MS多發于高緯度地區如北歐及英美等國,近年我國MS發病率有上升趨勢。MS的確切病因尚不清楚,可能與遺傳易感性、環境、病毒感染等因素有關。
在多數MS患者體內可檢測到多種抗髓鞘抗體,包括抗髓鞘堿性蛋白 (MBP)、髓鞘少突細胞糖蛋白(MOG)、抗蛋白脂蛋白(PLP)、抗髓鞘相關糖蛋白(MAG)等,其中抗MBP與多發性硬化發病較為密切,現已作為臨床輔助診斷和病情評估的重要指標。有報道表明HBV抗原的某些抗原表位與MBP的部分氨基酸序列有重疊交叉,因此推測HBV可以通過分子模擬機制誘發抗MBP的抗體并導致MS。Bogdanos DP等[15]通過對HBsAg和MS患者的MBP和MOG氨基酸序列分析發現HBsAg與后兩者存在某些高度同源序列,并且在實驗組可檢測到針對這些交叉序列的特異性抗體,該實驗表明在MS患者中的確存在HBV與自身抗原的交叉體液免疫應答。然而MS發病機制復雜,其中細胞免疫因素也至關重要,HBV是否在激活自身髓鞘反應的特異性T細胞方面發揮作用,該實驗并未做出結論。
2 HBV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的機理
自身免疫病的患者常常可以檢測到多種能與自身抗原成分反應的抗體以及活化的T淋巴細胞,其機制包括通過分子模擬、Bystander effects(旁觀者效應)、抗原表位擴增、刺激非抗原遞呈細胞高表達MHC分子等[2]誘發自身抗體和自身反應性T淋巴細胞活化進而導致自身免疫病的發生。HBV的某些抗原表位與機體自身的一些抗原成分相似,因此由這些抗原表位刺激產生的活性淋巴細胞與HBV作用的同時還要與機體的自身成分發生反應,此即為分子模擬。HBV還可以改變機體某些自身抗原成分的結構以破壞自身免疫耐受機制, 激活免疫系統導致自身免疫病的發生。除上述機制外,HBV還可以誘發機體不表達或低表達MHC細胞大量表達MHC I類分子,MHC I類分子可以將機體自身抗原遞呈給淋巴細胞引起自身免疫反應。
3 結語
病毒感染是自身免疫病發病的一個重要誘發因素已經被普遍接受,其中HBV與自身免疫病發病的關系研究雖然較多,但這些研究并未能完全闡釋清楚其具體機制,而且其中某些研究結果差異甚大,因此要得出HBV與自身免疫病發病的明確關系還需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Chi ZC,Ma SZ. Rheumatologic manifestations of hepatic diseases. HBPD Int,2003,2:32-37.
2 Maya R, Gershwin ME, Shoenfeld Y. Hepatitis B Virus(HBV)and Autoimmune Disease. Clinic Rev Allerg Immunol,2008,34:85-102.
3 Barzilai O, Ram M, Shoenfeld Y. Viral infection can induce the production of autoantibodies. Current Opinion in Rheumatology,2007,19:636-643.
4 劉燕婕,袁戎,胡麗華.乙型肝炎的自身抗體檢測分析及臨床意義.臨床血液學雜志,2009,22(6):289-292.
5 賀立香,黃德莊,閻惠平,等.乙型肝炎患者血清的自身抗體測定和臨床分析.中國國際醫學雜志,2001,1(4):325-327.
6 Guillevin L, Mahr A, Callard P, et al. Hepatitis B Virus-Associated Polyarteritis Nodos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utcome, and Impact of Treatment in 115 Patients.Medicine,2005,84(5):313-322.
7 Lau CF, Hui PK, Chan WM, et al. Hepatitis B associated fulminant polyarteritis nodosa: successful treatment with pulse cyclophosphamine,prednisolone and lamivudine following emergency surgery. 2002,14(5):563-566.
8 Auguet T, Barragan P, Ramirez R, et al. Lamivu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Polyarteritis Nodosa. Journal of Clinical Rheumatology,2007,13(5):298-299.
9 Alarcon - Segovia D, Fishbein E, Diaz - Jouanen E . Presence of hepatitis2associated antige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lin Exp Immunol,1972,12 :92191.
10 Ziegenfuss J F,Byrne EB,Stoloff IL,et al. Australia antigen in sys2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Lancet,1972,1 :8001
11 曹永獻,王斌,于秀英,等.系統性紅斑狼瘡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相互關系及細胞因子的調節作用.中華風濕病學雜志,2002,6(2):101-103.
12 仇寧,陳志強,蔡秀玲,等.系統性紅斑狼瘡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中國麻風皮膚病雜志,2001,17(1):19-20.
13 周明歡,歐強,譚德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與血清自身抗體的相關性.世界華人消化雜志,2004,12(3):607-609.
免疫病范文第2篇
記者隨機詢問就診患者:“湯主任看病這么慢,你們不著急啊?”那名患者隨口說道:“慢,說明他認真負責。我以前去過許多醫院,遇到的都是看病兩三分鐘的‘快刀手’專家,病情卻沒有起色。我就喜歡看病這么慢的專家。你看我今天又介紹了我的親戚一起來看湯主任的門診。”
難怪湯主任一個上午看30來名患者,卻經常從早上8點看到將近下午1點才結束。往往在這時,其他科室的專家早已下班,下午值班的其他專家也已經到崗了……
醫療質量是立身之本
出生于1965年12月的湯建平主任,雖剛屆50周歲,卻有著33年的臨床經歷。1983年7月,17周歲半的湯建平從江蘇徐州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后,踏上了內科醫師的漫漫征途。在江蘇泗陽縣人民醫院做了多年內科醫師并晉升主治醫師后,已有一定內科學功底的湯建平又于1994年9月跨入了蘇州大學醫學院的大門,開始了風濕免疫專科碩士研究生學習的新征程。1997年8月,湯建平以優異的碩士畢業成績,被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暨江蘇省人民醫院錄用,成為風濕免疫專科醫師。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在臨床工作中,湯建平時常以此古語自勉。“醫師是技術活,沒有仁術,何談仁心?”他深刻領悟了這句話的真諦,在臨床工作中時常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并細心觀察別的醫師的診治得失,以豐富自己的診治技術。
在江蘇省人民醫院工作5年后,湯建平積累了豐富經驗并晉升副主任醫師;2002年9月,他又進入上海交大醫學院,開始了在附屬仁濟醫院風濕免疫科攻讀博士學位的歷程。他的博士導師是時任中華風濕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仁濟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的顧越英教授。在讀博期間,他在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發表了5篇風濕免疫病學方面的論文,同時也跟著導師,在門診與病房大大提升了臨床能力。
2006年9月,湯建平在返回江蘇省人民醫院工作1年后,又遠涉重洋,奔赴美國洛杉磯,在著名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chool of Medicine(UCLA)開始了另一次正規的專職學習――做風濕免疫病學博士后研究。在美國期間,他開拓視野、博覽群書,系統研究了紅斑狼瘡、干燥綜合征的免疫機制與干細胞治療,發表了2篇SCI論文……
正是因為對醫療技術的不懈追求,如今,在湯建平的醫生辦公室與主任辦公室里,我們才能看到幾十面患者的感謝錦旗層層疊掛在墻面上,字里行間無不透露出他們對湯主任及其科室醫師團隊的推崇與感激之情。
事業平臺的建立是一生的追求
2008年8月,湯建平從美國UCLA回國后,舍棄了在原單位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優越工作與生活條件,以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身份,作為優秀人才被引進到了上海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開始籌建風濕免疫科。“創建自己的事業平臺,既是壓力挑戰,也是榮耀成就。”湯主任在回顧同濟醫院風濕免疫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8年歷程時欣慰地說。
科室初創時期,湯主任是唯一成員。“在醫院中層干部院周會開會時,我常說自己只是一個個體戶,是小本生意,請大家多多關照。院長卻說,有能力的個體戶以后都要發大財的。”湯主任風趣地說。那時他肩負風濕免疫科普通門診、專家門診、全院疑難病會診、學術講座、社區推廣宣傳、國內外專科學會交流等多重任務,沒日沒夜地工作。事實上,直到科室已有一定規模的今天,在他的主任辦公室里還有一張上下鋪高架床。“如果病房有危重患者,我晚上還是會睡在辦公室里,這樣心里才感到踏實。”
今天,同濟醫院風濕免疫科已經是同濟大學風濕免疫病學專業碩士生、博士生培養點,開放床位35張,在編醫師7名,均有博士或碩士學位,另有護士13名。科室以干燥綜合征、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與基礎研究為重點,目前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與上海市基金2項、國家“863”子課題協作單位1項;科室成員已發表風濕病研究論文60余篇,主編參編專著6部。其學科在上海市位居中等偏上規模,在全國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在臨床工作中,湯主任建立了本學科的醫療特色:一是“干燥綜合征的免疫平衡治療”,二是“類風濕關節炎的達標治療”,三是“紅斑狼瘡的免疫序貫治療”,四是“痛風的活血化瘀療法”。
醫生職業是非常辛苦的,除了繁重的臨床醫療工作、輪流值夜班,還有壓力更大的教學、科研課題申請、論文寫作等任務。“在中國的三甲醫院,一個合格的、有上進心的醫師每天起碼要工作10至12小時,并非其他行業的8小時工作制,多出來的幾個小時是義務奉獻。”湯主任自己的工作生活時間表就是真實寫照。他每天除了例行的醫療門診與病房查房之外,院內院外的會診、疑難病例討論、學術講座交流等已經把白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只有靠晚上加班,才能去做查閱疑難病例資料、教學課件準備、科研思路整理、論文寫作等工作。
“醫學的道路是艱辛的,有酸甜苦辣,也有懸壺濟世的成就感。盡管當前的醫療環境不是很理想,我還是無怨無悔。既然當初選擇了從醫,就會一直走下去。人總是要有建功立業的使命感的。”湯主任這樣表達了自己對醫學事業的奉獻精神與熱愛之情。
教學工作是
大學附屬醫院醫師的天職
醫生的職業是長周期教育培訓出來的:本科5年、碩士3年、博士3年,在大城市還要再規范化培訓2年,以后才能定工作崗位,沿著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的路線不斷晉升;同樣年齡的高中同學在工程領域已經是專家等級的時候,醫學院學生卻還在初級培訓階段,這一點社會上許多人并不知道。
“醫學教育是長周期高成本投入的精英教育。在歐美國家,4年文理科本科畢業后在醫學實驗室義務實習1年,經導師推薦合格,才有資格報考醫學院,5年出來直接獲得醫學博士(MD)學位,再經過intern、residency、fellow三個周期5年的培訓,才能有專科醫師執照,所以醫師35歲才能獨立執業,當然也有高收入回報的。”解析中美醫師教育機制的差距時,湯主任感慨地說。
作為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的帶教老師,湯主任每學年均會承擔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留學生全英文班學生的內科學與免疫學、醫學外語課理論教學任務。“在大學附屬醫院工作,帶教學生是我們的天職,也是我們有別于普通三甲醫院的特色與驕傲。”湯主任說,除了本科生教學,他還在招收碩士生、博士生。他建立了同濟大學醫學院風濕病學第一個博士點,目前已招收了6名碩士與1名博士。對研究生的畢業課題從選題、定方案、實驗環節的把控、經費預算、資料總結,到論文書寫、答辯、向雜志投稿,他無不幫學生把關。“教書育人是一種快樂,看著學生從懵懵懂懂變為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也是自己的一種成就。”湯主任如是闡述帶教學生的人生快樂哲學。
近些年,湯主任先后帶教過進修醫師、規范化培訓醫師、實習醫師50多名。他在門診看病、病房查房中言傳身教,為培養優秀醫師接班人不遺余力。
除了國內學生,湯主任先后帶教過朝鮮、尼泊爾、新加坡、馬來西亞、塞浦路斯的留學生,培養他們的臨床與科研技能。對此他說:“帶教外國學生也是相互學習的過程。同濟大學要走向國際,需要我們每個老師的奉獻。”
科研是醫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為醫師,在繁忙的臨床醫療工作之外,必須自己擠出時間去做科研。對于這一點,許多人難以理解。醫師看好病就行了,去折騰那些傷腦筋耗時的研究工作干嘛?“醫學的進步,無不是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相結合融合發展的結果。沒有研究,醫學仍將處在幾千年前的蒙昧巫師時代,所以在我國,醫師的職稱晉升一直與科研業績掛鉤。”湯主任對醫師做科研的意義如此詮釋說。
近些年,湯主任參加了國家“863”、“97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基礎研究5項,主持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基金、上海市基金3項,橫向合作課題2項。多年來,湯主任以風濕免疫科的一個疑難病種――干燥綜合征為臨床與基礎研究的主攻方向。這是一種全身外分泌腺上皮組織受到淋巴細胞廣泛浸潤與免疫復合物性血管炎為主要病理改變的自身免疫疾病,早期以口腔、眼睛干燥,牙齒部分發黑變質、咽喉干癢、皮膚干燥、起皮疹、關節酸痛、疲乏為癥狀,病情隱匿,因為無影響生命的損害出現,很多患者不拿它當回事兒;后期則引起肺間質纖維化、肺動脈高壓、腎小管酸中毒、腎小球損害、自身免疫性肝炎、血管炎、中樞神經與周圍神經炎、淋巴瘤等并發癥,導致患者失去工作能力,直至影響生命。
在臨床上,湯主任帶領科室醫師、研究生系統收集了200多例住院干燥綜合征患者的臨床病史、各個系統損害的癥狀體征、實驗檢查、影像檢查、細胞與體液免疫學的結果數據,建立了單中心的干燥綜合征患者數據庫,采用免疫平衡治療方法,使諸多患者擺脫了疾病困擾,重新返回了工作崗位。現在,他們已經建立了涵蓋上海、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山東等省份的一個較大規模的患者群。
在科研上,依托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的支撐,湯主任的幾屆研究生先后從T、B淋巴細胞免疫活化、分化、凋亡、增殖的體外實驗到干燥綜合征NOD模型小鼠的體內間充質干細胞治療、免疫細胞的micro-RNA表達譜變化與炎性細胞因子的作用通路機制,作了連貫性的系統研究。他們發現在干燥綜合征NOD模型小鼠的T細胞活化分化明顯亢進、炎性介質分泌增加、T細胞中的16個micro-RNA呈現高表達,而有6個micro-RNA呈現低表達。這些micro-RNA都參與體內免疫炎癥反應通路基因的表達調控。目前,他們正在通過計算機模擬篩選相關的micro-RNA分子與下游基因,準備做間充質干細胞治療干燥綜合征NOD模型小鼠的功能調控的實驗研究。
對于間充質干細胞治療自身免疫病,湯主任顯得很有信心:“干細胞分為實體干細胞和間充質干細胞兩大類。前者在國內外應用治療疾病動物模型和人體已經多年,都未能顯示出可復制性的臨床應用潛能,至今對于強烈的免疫排異反應的預防和控制效果有限,加上疾病機體原有的干細胞生長分化環境機制未搞清楚而無法調控;而間充質干細胞來源于胚胎中胚層,有分化潛能、在體內一定的環境下有可能分化為相應的實體細胞;不表達MHC-Ⅱ類分子而只低表達MHC-Ⅰ分子,后期的免疫排異反應基本沒有;更重要的是,它能誘導體內Treg/Th17細胞平衡,起到免疫抑制調節作用,因此對于免疫紊亂、免疫失耐受導致的自身免疫病特別有治療潛能。”
在同濟醫院風濕免疫科,近些年來,湯建平的團隊應用同濟大學干細胞臨床轉化中心按照GMP標準制作的臍帶間充質干細胞,治療了10余例對常規免疫抑制劑、糖皮質激素甚至生物制劑療效不佳的系統性紅斑狼瘡、干燥綜合征、皮肌炎、硬皮病等疑難風濕免疫病,發現患者的臨床癥狀、心肺肝腎功能、肢體關節活動度等臨床指標與血清IgG、IgA、IgM、CH50、C3、C4、ANA、dsDNA、CD4、CD8、CD56等免疫學指標都有明顯的改善。他們已經收集患者治療前后的血液細胞組分與血清樣本,準備做相關基因芯片檢測,以找出間充質干細胞發揮免疫調節效應的關鍵路通分子,為以后的靶點治療分子篩選累積素材。
事實上,湯主任的大部分業余時間是在閱讀科研文獻、撰寫論文、指導研究生,以及申請各類課題和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等活動中度過的。記者在他的辦公室看到,辦公桌上、櫥柜中、值班床頭,都擺放著大部頭的醫學專著。在他的辦公電腦網頁列表中所見到的,大多也是國內外的醫學網站主頁。在湯主任的帶領下,全科醫師都在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道路上不斷地前進著。“研究就是學習。前人的醫療實踐經驗只有通過科學的方法傳承,才能變成科學的醫學積累。無科學方法指導下的醫學實踐只能是盲目的經驗總結,不具有可復制性。”湯主任對醫學科研的作用,給出了這樣的定位。
“站在上海這個中國科技高地上,通過同濟大學這個大平臺的鋪墊與我們全科人員的勤奮努力,相信我們會在將來成為全國知名的醫療、教學、科研齊頭并進的大學附屬醫院風濕免疫學科。”湯建平主任最后說。
免疫病范文第3篇
CD是攜帶有遺傳易感基因的個體因攝入含麩質蛋白的谷物及其制品而誘發的自身免疫性腸病。歐洲人CD的發生率為1%[1]。HLA-DQ2 (DQA1*0501-DQB1*0201) 和HLA-DQ8 (DQA1*0301-DQB1*0302) 基因單倍型幾乎出現于所有的乳糜瀉患者, 但大部分攜帶有HLA-DQ2和HLA-DQ8基因單倍型的個體并不發展為乳糜瀉, 意味著還有未確認的遺傳因素參與了乳糜瀉的發生[1]。DQA1*05:01和DQB1*02:01是最主要的風險基因[2]。Piancatelli等使用聚合酶鏈式反應-序列特異性引物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equence-specific primer, PCR-SSP) 對HLA進行基因分型發現DQ2.2和DQ2.5在摩洛哥CD患者出現的頻率較正常對照高, 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而DQ8在摩洛哥CD患者和正常對照之間出現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與HLA-DQ2.5/X (X指等位基因位點為非DQ2.5) 雜合子個體相比, HLA-DQ2.5純合子個體具有更高的患CD風險, 這是由于HLA-DQ2.5表達在抗原呈遞細胞表面并使其更有效地進行麩質提呈, DQB1*02純合子對CD嚴重程度的影響已被證實[3]。DR3-DQ2、DR7-DQ2基因單倍型與摩洛哥人CD有關[3]。Senapati等[4]發現HLA-DQ2.2 (rs2395182等位基因T) 、HLA-DQ2.2 (rs7775228等位基因T) 、HLA-DQ2.5 (rs2187668等位基因A) 、HLA-DQ4 (rs4713586等位基因T) 、HLA-DQ8 (rs7454108等位基因T) 可以增加患CD的風險。Bibb等[5]發現乳糜瀉患者更常伴發其他自身免疫病, 其中橋本甲狀腺炎排在首位, 其次是1型糖尿病和牛皮癬, 這種關聯可能是上述疾病有著共同的遺傳易感基因位點, 比如HLA-DR3、DQ2, 并且發現CD與慢性自身免疫病的發生有關。
表1 HLA介導的常見自身免疫病及相關的HLA等位基因及單倍型Tab.1 HLA-mediated common autoimmune diseases and their associated alleles and haplotypes
2.2 系統性紅斑狼瘡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與HLA的相關性
SLE是一種累及多系統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特征在于產生抗核抗體, 導致組織炎癥和器官損傷。目前已發現遺傳因素與SLE的發生和發展有關, 尤其以HLA與SLE的關系最為密切。徐丹萍等[6]發現SLE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中HLA-G分子較正常人表達量減少。Mitsdoerffer等[7]發現多發性硬化患者單核細胞膜表面表達的HLA-G分子較正常人顯著降低, 另外, 1型糖尿病也有此現象。Rizzo等[8]對SLE患者和正常人對照研究發現:HLA-G第8個外顯子14 bp插入 (+14 bp) 等位基因頻率和純合子插入 (14 bp+/+) 基因型頻率都較正常對照顯著升高, 而缺失純合子 (14 bp-/-) 基因型頻率較正常對照顯著降低, 提示14 bp片段的多態性是SLE的潛在風險因素。HLA-DR3 (DRB1*03:01-DQA1*05:01-DQB1*02:01) 和DR15 (DRB1*15:01/03-DQA1*01:02-DQB1*06:01) 是SLE的風險基因單倍型, 且兩者存在一定的連鎖, DRB1*03:01、DQA1*04:01、DQA1*05:01、DQA1*01:02、B*08:01、B*18:01是SLE的風險基因, DRB1*01:02、DRB1*12:01、DQA1*01:04、DQB1*03:02、C*04:01是SLE的保護基因, HLA-DQB1位點rs9273448等位基因A也是SLE的一種保護性因素[9]。Fernando等[10]發現西班牙SLE患者與HLA-DRB1*03:01、DRB1*15:01、DRB1*08:01有關, 日本SLE患者與DRB1*15:01有關, 且HLA-DRB1*15基因亞型分布呈現地域差異, 在歐洲人中常見的等位基因是HLA-DRB1*15:01, 太平洋和東南亞人群常見的等位基因是HLA-DRB1*15:02, 而在非洲人群中是HLA-DRB1*15:03。Bettencourt等[11]發現DRB1*13是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系統性硬化癥共同的保護基因, DRB1*03是系統性紅斑狼瘡、多發性硬化、重癥肌無力共同的風險基因, DRB1*09是系統性紅斑狼瘡、多發性硬化、類風濕性關節炎共同的保護基因。
2.3 類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與HLA的相關性
RA是一種以關節滑膜增生和軟骨破壞為特征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病, 遺傳與HLA-DRB1關系最為密切, 與RA相關的DRB1等位基因編碼的DR分子鏈的第3高變區第70~74位氨基酸有著QKRAA (谷氨酸-賴氨酸-精氨酸-丙氨酸-丙氨酸) 、QRRAA (谷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丙氨酸) 或RRRAA (精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丙氨酸) 共同序列, 其不僅增加了個體患RA的風險, 而且還使個體表現為發病呈年輕化的趨勢, 更嚴重的骨侵蝕和產生抗瓜氨酸化蛋白抗體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ies, ACPA) , 此外RA患者關節炎骨破壞的嚴重程度與HLA-DRB1等位基因編碼的共同序列的數目呈正相關[12]。HLA-DRB1分子第11位氨基酸是亮氨酸或者纈氨酸則增加患RA的風險, 第11位氨基酸是絲氨酸則減少患RA的風險[13]。陳佳喜等[14]發現RA患者外周血s HLA-G和調節性T細胞比正常人顯著降低, RA患者用甲氨蝶呤治療后, HLA-G的表達顯著升高。李長紅等[15]發現RA患者與正常對照相比, HLA-G14 bp插入/缺失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頻率差異在兩組間無統計學意義;而RA抗核小RNA蛋白 (snRNP) 抗體、抗組蛋白抗體陽性患者與抗snRNP抗體、抗組蛋白抗體陰性患者相比, HLA-G 14 bp插入/缺失多態性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抗snRNP抗體陽性組+14 bp等位基因與+14 bp/-14 bp雜合子基因型頻率較抗snRNP抗體陰性組顯著增加, 抗組蛋白抗體陽性組-14 bp等位基因與-14 bp/-14bp純合子基因型頻率較抗組蛋白抗體陰性組顯著增加。Tokunaga等[16]發現歐洲人RA相關性最強的HLA-DR4亞型是DRB1*04:01, 日本人RA相關性最強的HLA-DR4亞型是HLA-DRB1*04:05。Trier等[17]發現HLA-DRB1*04:01/04/05/08/09、DRB1*01:01/02、DRB1*10:01、DRB1*14:02是RA的風險基因。Achour等[18]應用Taqman基因分型方法發現rs6457617 (位于HLA-DQB1) TT基因型與突尼斯人RA的易感性有關, rs6457617*T-HLA-DRB1*04+單倍型明顯增加突尼斯人患RA的風險, rs6457617與HLA-DRB1存在著一定的連鎖, rs6457617T等位基因和TT基因型有著更高的抗環瓜氨酸抗體, 而rs13192471 (位于HLA-DRB1) 與RA的易感性和嚴重程度無關。
2.4 強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 與HLA的相關性
AS是一種致畸的慢性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主要影響脊柱和骶髂關節, 其次還會影響外周關節和眼睛、腸道、皮膚等, 漢族人群的患病率為0.2%~0.54%, 男女患病比為 (2~3) ∶1[19]。遺傳以HLA-B27關系最為密切, HLA-B27通過分子模擬機制和蛋白錯誤折疊參與AS的病理過程。Sheehan等[20]發現HLA-B*27:05幾乎存在于所有種族中, 推斷它可能是祖先型等位基因。高加索人與AS相關的主要亞型是HLA-B*27:05和HLA-B*27:02, 亞洲人與AS相關的亞型主要是HLA-B*27:04和HLA-B*27:07, 在地中海人群中是HLA-B*27:02[21]。HLA-B*60與英國HLA-B27陽性的AS患者有關[22], HLA-B*60和HLA-B*61與臺灣HLA-B27陰性的AS患者有關[23], HLA-B*39與日本HLA-B27陰性的AS患者有關[24]。目前發現了除HLA-B27以外與AS相關的基因:HLA-B*51:01、HLA-B*47:01、HLA-B*40:02、HLA-B*13:02、HLA-B*40:01, 它們可以增加個體患AS的風險, HLA-B*07:02、HLA-B*57:01可以減少患AS的風險[25], 其中HLA-B*51是脊柱關節炎相關疾病的遺傳風險因素, 同時也是白塞病的風險因素, 因此推斷可能有著共同的發病機制[19]。進一步陸續發現了除HLA-B位點以外和AS相關的基因:比如HLA-A*02:01、HLA-DPB1、HLA-DRB[25]。姜芳等[26]發現HLA-B27表達水平與基質金屬蛋白酶 (骨侵蝕重要蛋白水解酶家族) 表達水平呈正相關, 在亞洲人中主要以HLA-B*27∶04為主。代東發等[27]發現以HLA-B*27∶04與AS的關聯性最強, 其次是B*27∶02、HLA-B*27∶05、B*27∶07。李苗等[28]發現HLA-B27可能會影響腸道菌群, 進而產生大量的細胞因子介導免疫細胞, 進而產生自身免疫反應。Wang等[29]發現HLA-C*12:02:02與臺灣AS有關。
2.5 1型糖尿病 (Type 1 diabetes, T1D) 與HLA的相關性
T1D屬于多基因遺傳性疾病, 主要影響產生胰島素的細胞并導致終身依賴于外源性胰島素。研究報道, DRB1*03-DQA1*05-DQB1*02 (DR3-DQ2) 和DRB1*0401/2/4/5-DQA1*0301-DQB1*0302 (DR4-DQ8) 的兩種HLAⅡ類DR-DQ單倍型與T1D的發生顯著相關, 特別是DR3-DQ2也與多種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關[30]。楊麗等[31]發現T1D患者HLA-DRB1*04頻率較正常人高, 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HLA-DRB1*15、HLA-DRB1*16是T1D的保護基因。Reinauer等[32]發現DRB1*03:01-DQA1*05:01-DQB1*02:01 (DR3-DQ2) 、DRB1*04-DQA1*03:01-DQB1*03:02 (DR4-DQ8) 、DRB1*04:05-DQA1*03:01-DQB1*02:02、DRB1*08:01-DQ A1*04:01/02-DQB1*04:02 (DR8-DQ4) 基因單倍型與T1D有關, DRB1*07:01-DQA1*02:01-DQB1*02:02和DRB1*13:01-DQA1*01:02-DQB1*06:03是T1D的保護性基因單倍型, 它在T1D人群中出現頻率較低。Fagbemi等[33]通過PCR-SSP基因分型方法發現DR3、DR3-DR4是T1D的風險基因單倍型, DQA1*05:01、DQB1*02:01是T1D的風險基因, DR3、DR3-DR4、DQA1*05:01、DQB1*02:01使得患T1D的風險增加3~14倍, DR4、DQB1*03:02、DQB1*06:02在T1D患者與正常對照組之間出現的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DQA1*05:01是T1D的風險基因, 同樣的結論也出現在法國、巴西、西班牙T1D人群[33]。
2.6 多發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MS) 與HLA的相關性
MS是一種由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多基因遺傳性疾病, 臨床特征以神經脫髓鞘改變為主, 且年輕女性多見。Shahbazi等[34]應用PCR-SSP基因分型方法對伊朗MS患者與健康對照組研究發現:HLA-DRB1*15與IL-10的基因多態性與MS易感性相關, 并且DRB1*15等位基因與IL-10多態性的相互作用可能在MS的易感性中起重要作用。Moutsianas等[35]應用Meta分析發現HLA-DRB1*15:01、HLA-DRB1*13:03、HLA-DRB1*03:01、HLA-DRB1*08:01、HLA-DQB1*03:02是歐洲人群MS的風險基因, HLA-A*02:01、HLA-B*44:02、HLA-B*38:01、HLA-B*55:01是歐洲人群MS的保護性基因, 在DRB1*15:01存在的情況下HLA-DQA1*01:01對歐洲人群MS有著強烈的保護作用。Nakamura等[36]對HLA-DRB1進行基因分型發現:DRB1*04:05、DRB1*15:01是日本人群MS的風險基因, DRB1*01:01、DRB1*09:01、DRB1*13:02、DRB1*15:02是日本人群MS的保護基因, HLA-DRB1*08:01在日本人群MS患者與正常對照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對HLA-DRB1*04:05和緯度對日本人群MS疾病嚴重程度的影響研究發現:HLA-DRB1*04:05可以減少MS患者大腦損傷情況和腦脊液Ig G的異常程度, 而高緯度與HLA-DRBI*0405有著相反的作用。Andlauer等[37]發現DRB1*15:01、DRB1*13:03、DRB1*03:01、DRB1*08:01、DPB1*03:01是德國人群MS的風險基因, A*02:01、B*38:01是德國人群MS的保護性基因。
3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 自身免疫病是一類涉及遺傳和環境的復雜疾病, 從遺傳角度HLA基因與自身免疫病的發生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HLA基因通過影響基因表達水平最后導致個體發生自身免疫病, 因此個體的HLA分型對于診斷和治療某種自身免疫病有著重要的意義。目前自身免疫病相關的HLA主要為經典HLAⅡ類基因, 部分HLAⅠ類基因區也有所涉及, 尤其以HLA-G基因與自身免疫病的相關性研究的最多。隨著高通量測序的應用, 人們發現一個自身免疫病可能與多個HLA位點有關, 一個HLA位點可能參與多個自身免疫病的發生, 因此尋找自身免疫病特異的HLA位點以及各個自身免疫病共有的風險基因顯得尤為重要, 這將對自身免疫病的發病機制、早期診斷和特異性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 Patel B, Wi CI, Hasassri ME, et al.Heterogeneity of asthma and the risk of celiac disease in children[J].Allergy Asthma Proc, 2018, 39 (1) :51-58.
[2] Philip Deitiker, Zouhair Atassi.MHC genes linked to autoimmune disease[J].Crit Rev Immunol, 2015, 35 (3) :203-252.
[3] Piancatelli D, Barhdadi IBE, Oumhani K, et al.HLA typing and celiac disease in moroccans[J].Med Sci (Basel) , 2017, 5 (1) :2-2.
[4] Senapati S, Sood A, Midha V, et al.Shared and unique common genetic determinants between pediatric and adult celiac disease[J].BMC Med Genomics, 2016, 9 (1) :44-44.
[5] BibbS, Pes GM, Usai-Satta P, et al.Chronic autoimmune disorders are increased in celiac disease:A case-control study[J].Medicine (Baltimore) , 2017, 96 (47) :e8562.
[6]徐丹萍, 林愛芬, 顏衛華.HLA-G與自身免疫病相關性研究進展[J].生命科學, 2012, 24 (3) :217-222.Xu DP, Lin AF, Yan W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LA-G and autoimmune diseases[J].Chn Bullt Life Sci, 2012, 24 (3) :217-222.
[7]Mitsdoerffer M, Schreiner B, Kieseier BC, et al.Monocyte-derived HLA-G acts as a strong inhibitor of autologous CD4 T cell activation and is upregulated by interferon-in beta vitro and in vivo:rationale for the therapy of multiple sclerosis[J].J Neuroimmunol, 2005, 159 (1-2) :155-164.
[8]Rizzo R, Hviid TV, Govoni M, et al.HLA-G genotype and HLA-Gexpressi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HLA-G as a putative susceptibility gen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Tissue Antigens, 2008, 71 (6) :520-529.
[9] Langefeld CD, Ainsworth HC, Cunninghame Graham DSC, et al.Transancestral mapping and genetic load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Nat Commun, 2017, 8:16021.
[10] Fernando MMA, Jan F, Annette L, et al.Transancestral mapping of the MHC regi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dentifies new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ing loci at MSH5, HLA-DPB1 and HLA-G[J].Ann Rheum Dis, 2012, 71 (5) :777-784.
[11]Bettencourt A, Carvalho C, Leal B, et al.The protective role of HLA-DRB1*13 in autoimmune disease[J].J Immunol Res, 2015, 2015 (1) :948723.
[12] Van DV, Holoshitz J.A reciprocal HLA-disease association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pemphigus vulgaris[J].Front Biosci (Landmark Ed) , 2017, 22:909-919.
[13] Viatte S, Barton A.Genetic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susceptibility, severity, and treatment response[J].Semin Immunopathol, 2017, 39 (4) :395-408.
[14]陳佳喜, 沈波.HLA-G與類風濕性關節炎相關關系的研究進展與趨勢[J].醫學研究雜志, 2012, 41 (1) :169-172.Chen JX, Shen B.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LA-G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J].J Med Res, 2012, 41 (1) :169-172.
[15]李長紅, 魏琴, 李坤, 等.人類白細胞抗原G14bp插入/缺失多態性和風濕性疾病自身抗體產生的相關性研究[J].山西醫藥雜志, 2017, 46 (23) :2845-2848.Li CH, Wei Q, Li K, et al.Association of HLA-G 14bp insertion/deletion polymorphism with autoantibody production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diseases[J].Shanxi Med J, 2017, 46 (23) :2845-2848
[16] Tokunaga K.Lessons from genome-wide search for disease-related gen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LA-disease associations[J].Genes (Basel) , 2014, 5 (1) :84-96.
[17] Trier N, Izarzugaza J, Chailyan A, et al.Human MHC-II with shared epitope motifs are optimal epstein-barr virus glycoprotein42 ligands-relation to rheumatoid arthritis[J].Int J Mol Sci, 2018, 19 (1) :317-317.
[18] Achour Y, Ben HM, Chaabane S, et al.Analysis of two susceptibility SNPs in HLA region and evid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s64576175 on Tunisian rheumatoid arthritis[J].J Genet, 2017:911-918.
[19] Li Z, Brown MA.Progress of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J].Clin Transl Immunol, 2017, 6 (12) :e163.
[20] Sheehan NJ.HLA-B27:whats new?[J].Rheumatology, 2010, 49 (4) :621-631.
[21] Taurog JD.The mystery of HLA-B27:If it isnt one thing, its another[J].Arthritis Rheum, 2007, 56 (8) :2478-2481.
[22]Brown M, Bunce M, Calin A, et al.HLA-B associations of HLA-B27 negative ankylosing spondylitis:comment on the article by Yamaguchi et al[J].Arthritis Rheum, 2014, 39 (10) :1768-1769.
[23] Wei JC, Tsai WC, Lin HS, et al.HLA-B60 and B61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HLA-B27-negative Taiwan Chinese patients[J].Rheumatology (Oxford) , 2004, 43 (7) :839-842.
[24] Yamaguchi A, Tsuchiya N, Mitsui H, et al.Association of HLA-B39 with HLA-B27-negative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pauciarticular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Japanese patients.Evidence for a role of the peptide-anchoring B pocket[J].Arthritis Rheum, 1995, 38 (11) :1672-1677.
[25] Cortes A, Pulit SL, Leo PJ, et al.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association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re complex and involve further epistasis with ERAP1[J].Nat Commun, 2015, 21;6:7146-7146.
[26]姜芳, 許敏.強直性脊柱炎患者基質金屬蛋白酶和人白細胞抗原B27的表達分析[J].現代醫藥衛生, 2017, 33 (24) :3741-3744.Jiang F, Xu M.Analysis o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and HLA-B27 in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J].JMod Med Health, 2017, 33 (24) :3741-3744.
[27]代東發, 孫玉英.HLA-B27分子及其與強直性脊柱炎關聯的研究進展[J].生物技術通訊, 2014, 25 (1) :118-121.Dai DF, Sun YY.Research progress of HLA-B27 and its associate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J].Letters Biotechnology, 2014, 25 (1) :118-121.
[28]李苗, 孫迪, 付冰冰, 等.腸道菌群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進展[J].中國微生態學雜志, 2015, 27 (10) :1233-1237.Li M, Sun D, Fu BB, et al.Research on gut microbiota and autoimmune disease:progress review[J].Chin J Microecol, 2015, 27 (10) :1233-1237.
[29] Wang C M, Wang S H, Jan Wu Y J, et al.Human Leukocyte Antigen C*12:02:02 and Killer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2DL5 are Distinctly Associated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the Taiwanese[J].Int J Mol Sci, 2017, 18 (8) :1775-1775.
[30] Parkkola A, Laine A P, Karhunen M, et al.HLA and non-HLAgenes and familial predisposition to autoimmune diseases in families with a child affected by type 1 diabetes[J].Plos One, 2017, 12 (11) :e0188402.
[31]楊麗, 劉金慧, 韓蓓, 等.妊娠期糖尿病胰島自身抗體陽性與HLA-DRB1基因型相關探析[J].糖尿病新世界, 2016, 19 (22) :1-2.Yang L, Liu JH, Han B, et al.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abetes islet antoantibody positive in the gestation period and HLA-DRB1 genotype[J].Diabetes New World, 2016, 19 (22) :1-2.
[32] Reinauer C, Rosenbauer J, Bchle C, et al.The clinical course of patients with preschool manifestation of type 1 diabetes is independent of the HLA DR-DQ genotype[J].Genes (Basel) , 2017, 8 (5) :146-146.
[33] Fagbemi K A, Tcm M, Azonbakin S, et al.HLA class II allele, haplotype, and genotype associations with type 1 diabetes in benin:a pilot study[J].J Diabetes Res, 2017, 2017 (6) :1-4.
[34] Shahbazi M, Jsa A, Roshandel D, et al.Combination of interleukin-10 gene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HLA-DRB1*15 allele i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sclerosis[J].Indian J Med Res, 2017, 145 (6) :746-752.
[35] Moutsianas L, Jostins L, Beecham A H, et al.Class II HLA interactions modulate genetic risk for multiple sclerosis[J].Nat Genet, 2015, 47 (10) :1107-1113.
免疫病范文第4篇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其病因和發病機制仍不清楚,目前大多學者認為腸黏膜免疫調節異常,持續腸道感染,腸黏膜屏障缺損,遺傳和環境等因素共同參與了疾病發生過程[1~3]。CD主要病理學表現為整個腸壁黏膜組織肉芽腫性炎癥,多發生在回腸末端和升結腸段,也可發生在口腔、食管、胃和區;而UC僅限于結腸,少部分患者可累及回腸末端,主要表現為結腸壁淺表黏膜組織炎癥,可出現潰瘍和急性膿性白細胞浸潤。
研究發現,腸黏膜先天性免疫應答(innate immunity)和獲得性免疫應答(adaptive immunity)共同參與了IBD的病理生理發生過程[1~4]。因此,了解腸道黏膜組織的先天性和獲得性免疫應答對腸道黏膜組織炎癥反應,抵抗腸道細菌感染,清除腸道病原微生物對機體的危害,以及IBD的發病機制等有重要意義。先天性免疫應答是機體在長期發育和進化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系列防御功能,能夠非特異地阻擋或清除入侵體內病原微生物及體內出現的突變、衰老和死亡細胞[5]。先天性免疫應答是機體在外界抗原刺激條件下形成的非特異性的免疫反應,可迅速或數小時后形成,以清除病原體的侵入,是機體先天固有的。而獲得性免疫應答是抗原特異性防御機制,在抗原刺激數天后形成免疫保護,以清除體內特異性抗原,通常終生伴隨[6]。腸道先天性免疫系統由生理性屏障、腸黏膜組織內補體系統、各種細胞(腸上皮細胞、肥大細胞、中性粒細胞、單核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NK細疫應答的細胞通過分泌一些抗炎癥細胞因胞)、細胞因子及趨化因子組成。這些參與腸道先天性免子(TNFα、IL1)、活性氧和抑菌肽等,吞噬、清除侵入的病原微生物[5]。
腸腔內存在大量的細菌,這些細菌既是營養腸道的必需菌,又具有促使腸道發育、阻止腸道病原微生物感染的作用。腸黏膜組織先天性免疫系統識別細菌抗原對維持黏膜內環境的穩定,尤其是保持腸黏膜免疫耐受狀態起著重要作用。若打破腸黏膜組織內免疫耐受,將造成腸道黏膜炎癥損傷、食物過敏反應、致病性微生物感染等[4~6]。當食物或細菌抗原接觸胃腸道后,大部分抗原成分主要由腸集合淋巴結表面的M細胞吸收,還有少部分通過腸道黏膜固有層內樹突狀細胞的突觸直接伸向腸腔內攝取,以及通過上皮細胞間的縫隙直接吸收,進而引起一系列的腸黏膜局部免疫反應,誘導腸道黏膜免疫耐受,即對食物抗原不應答。若打破此免疫耐受狀態,可以引起食物過敏反應或炎癥損傷[7,8]。當腸道內細菌或食物抗原通過腸腔面的M細胞或通過其他途徑吸收進入集合淋巴結及腸黏膜固有層后,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將抗原加工處理后傳遞至集合淋巴結的生發中心或腸黏膜固有層的淋巴細胞。在TGFβ、IL4、IL5、IFNγ和抗原刺激下,B淋巴細胞增殖并轉化成細胞表面含IgG、IgA、IgE等特異性漿細胞,而T淋巴細胞激活分化成免疫效應細胞(包括Th1、Th2、Th17細胞、CTL細胞)。在生理情況下,活化的CD4+ T細胞主要以Th2形式、少部分以Th3、Tr1、Treg細胞形式存在,構成腸黏膜免疫保護作用。通常上述激活的淋巴細胞僅小部分直接分散在黏膜固有層內,而大部分經淋巴循環進入腸系膜淋巴結,再通過淋巴循環(胸導管)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最后歸巢于腸道黏膜組織固有層內,參與黏膜免疫調節。sIgA是胃腸道和黏膜表面主要的免疫球蛋白,對消化道黏膜防御起著重要的保護作用。腸腔內sIgA通過結合細菌將腸道內細菌聚集起來,形成抗原抗體復合物并刺激腸道粘液的分泌以及加速粘液在腸黏膜表面的移動,有助于排除腸道中的細菌和內毒素[7,8]。
腸黏膜先天性免疫系統擁有識別腸腔內微生物抗原能力,這類微生物抗原稱為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MP),而機體防御細胞(如吞噬細胞)表達有識別PAMP的相應受體,即模式識別受體(PRR)[9,10]。Toll樣蛋白受體(TLR)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NOD)蛋白是重要的PRR,主要表達在一些免疫細胞(如B、T細胞、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胞、中性粒細胞)及腸黏膜上皮細胞上,識別相應的病原微生物抗原后,激活細胞內一系列信號,誘導細胞核內轉錄因子NFκB激活,促使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等釋放,引起免疫應答[9,10]。近來研究發現TLR4在IBD患者腸上皮細胞和固有層單核淋巴細胞上表達升高,IFNγ和TNFα可上調其表達。TLR4和TLR5基因變異與一些IBD患者的疾病發展有密切關系,可能促使腸黏膜組織內Th1細胞激活,造成黏膜炎癥損傷[11,12]。NOD2是CD的易感基因之一,其基因突變使其不能識別細菌胞壁酰二肽抗原,致使NFκB活性下降,引起腸黏膜抑制細菌感染能力下降,導致腸道黏膜炎癥損傷[13]。NOD2基因突變還引起腸黏膜內潘氏細胞分泌防御素降低,導致腸道菌群清除異常,誘導腸黏膜組織內巨噬細胞激活,分泌大量IL12和IL1β,引起腸黏膜組織以Th1為主的炎癥反應。另外,NOD2突變可使細胞凋亡機制失常,導致CD患者腸黏膜慢性炎癥和組織破壞,與患者的臨床類型(纖維化、狹窄)有關。
腸道黏膜組織內各種淋巴細胞受到腸道病原微生物抗原特異性激活是IBD免疫病理學的重要特征。已有研究發現在IBD患者炎癥腸道黏膜組織內有大量激活的免疫細胞浸潤,如CD69+ CD40L+ T、CD25+ NK細胞、CD40+ CD80+ B、CD68+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 [1~3];腸黏膜組織內淋巴細胞和一些基質細胞(如成纖維細胞)表達高水平的黏附分子和輔助信號分子(如CD54、CD62L、CD106、RANKL、41BB)。這些免疫細胞在炎癥狀態下還可表達高水平的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受體(如CCR5、CCR6、CCR9)、整合素(如α4β7 integrin)等,而腸黏膜組織內毛細血管內皮細胞及成纖維細胞表面表達高水平的趨化因子、選擇素(如Eselectin、Pselectin)和CD54(ICAM1)等,這些分子間的相互作用進一步誘導血液循環中的白細胞向腸黏膜組織內移動、歸巢、浸潤,促使局部炎癥應答[1~3]。CD患者炎癥腸黏膜組織內CD4+ T細胞經體外刺激后產生大量Th1效應的促炎癥細胞因子(如IFNγ、TNFα、IL2);而UC患者炎癥腸黏膜組織內CD4+ T和NKT細胞可分泌大量Th2效應細胞因子(如IL4、IL13)。近年來,在CD患者炎癥腸黏膜內也發現有其他促炎癥細胞因子表達,如IL12、IL15、IL18、IL23以及分泌IL17的Th17細胞,這些促炎癥細胞因子可進一步放大局部免疫應答,參與CD患者腸黏膜免疫病理反應[1~3,14,15]。因此,腸黏膜組織內異常免疫應答(即Th1/Th2免疫平衡失調)在IBD患者腸道炎癥發生過程中起重要作用[1~3]。
免疫病范文第5篇
為切實做好今年重大動物疫病免疫工作,緊緊按照“應免盡免、不留空檔”的總體要求,對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芻獸疫、布魯氏桿菌等4種疫病進行強制免疫,對H7N9做好流行病學調查和監測工作,有效控制重大動物疫情的發生和傳播,確保不發生區域性重大動物疫病,根據國家和省、市、縣動物疫病強制免疫計劃,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標任務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
對所有雞、水禽(鴨、鵝)和人工飼養的鵪鶉、鴿子等禽只進行高致病性禽流感強制免疫,群體免疫密度應達到并維持在90%以上,其中應免禽免疫密度必須達到100%,免疫抗體合格率必須達到并維持70%以上。
(二)口蹄疫
對所有豬進行O型口蹄疫強制免疫;對所有牛、羊進行O型和亞洲I型口蹄疫強制免疫;對所有奶牛在進行O型和亞洲Ⅰ型口蹄疫強制免疫的基礎上,還必須進行A型口蹄疫免疫。群體免疫密度應達到并維持在90%以上,其中應免牲畜免疫密度必須達到100%,免疫抗體合格率必須達到并維持70%以上。
(三)小反芻獸疫
對所有羊使用小反芻獸疫疫苗進行強制免疫,群體免疫密度應達到并維持在90%以上,其中應免羊免疫密度必須達到100%,免疫抗體合格率應達到70%以上。
(四)布魯氏菌病
今年根據上級政策文件精神,布魯氏菌病防疫要本轄區布病疫情的實際情況,在申請縣級以上相關專家充分論證和科學評估后對牛、羊實施分類免疫。布病防治按照農業部《常見動物疫病免疫推薦方案(試行)》執行,在疫病采樣監測基礎上開展免疫,牛、羊每年免疫1次,1次1頭份。牛羊種公畜禁止免疫。奶畜的免疫,個體病原陽性率超過2%的鄉鎮,或個體陽性率大于5%的場群,由縣級獸醫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報省畜牧局批準后實施免疫。
(五)豬瘟和高致病性豬藍耳病
今年豬瘟和高致病性豬藍耳病暫不列為強制免疫病種,但仍然為國家規定的一類動物疫病,各項防控措施不能有任何放松。根據流行狀況和監測評估結果,制定實施本轄區的免疫方案,并做好免疫效果監測和評價。要進場入戶進行宣傳,告知其強制免疫政策調整情況,按一類病要求,指導其加強防治,強化其主體責任和主動免疫。
(六)雞新城疫
對所有雞實施新城疫全面免疫,群體免疫密度應達到并維持在90%以上,其中應免雞免疫密度必須達到100%,免疫抗體合格率達到并維持70%以上。
二、時間安排
今年春季集中免疫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集中免疫階段,5月5日前,各村委組織防疫隊伍,集中力量,全面突擊,力爭基本完成集中免疫任務;第二階段為補免補防階段,5月10日前,各村委開展查漏補缺、補免補防工作,進行自查和免疫效果評估;第三階段為檢查驗收階段,5月15日后,將接受全縣統一組織考核驗收。
三、具體要求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芻獸疫免疫
嚴格按照國家有關動物疫病強制免疫計劃執行。規模養殖場按推薦免疫程序進行免疫,散養畜禽實施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補免。有條件的地方,散養畜禽可參照規模養殖場的免疫程序進行免疫。
(二)布魯氏菌病免疫
今年春季不集中免疫,但要進行全面監測,所有種畜和奶畜每年至少開展一次檢測,對其它牛羊每年至少開展一次抽檢,發現陽性畜的場群應進行逐頭檢測。各村委要按時完成采樣送檢任務。
四、免疫效果監測
堅持全面監測和重點監測相結合、集中監測和日常監測相結合的原則,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芻獸疫、高致病性藍耳、豬瘟、新城疫等動物疫病的免疫抗體監測,科學評估和指導免疫工作,對于群體免疫抗體水平合格率低于70%的畜禽,及時進行加強免疫,切實構筑起免疫保護屏障。春季集中監測應在5月5日前全面完成任務,務必實現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芻獸疫、布魯氏菌病四種強制免疫病種免疫抗體合格率高于70%。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
從當前疫情形勢看,重大動物疫病總體仍呈疫源分布廣、毒株變異快、外疫威脅大等新特點,國內外新病毒不斷出現,交替流行,傳統病毒、變異病毒以及不同亞型病毒同時存在。面對嚴峻形勢,各村委要高度重視,保持高度警惕,各村支部書記是動物防疫工作的第一責任人,要對防疫工作和疫情報告控制負總責,村級防疫員是直接責任人,具體負責防疫工作的組織實施,認真解決防疫過程中的具體問題,要站在講政治的高度,抱著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搞好動物防疫工作,同時要求各村委必須確定一名村干部具體負責工作落實,切實加大對動物防疫工作的投入力度,防疫結束后,鎮將組織人員對各村委的防疫情況考核驗收,通過防疫簡報、會議通報等形式,激勵先進,督促后進,強力推進春季集中免疫工作有力有序有效開展,全面完成今年春季的動物防疫工作任務。
(二)堅持動物防疫工作責任制
鎮農業中心與村級動物防疫員簽訂動物防疫工作合同書,定期對村級動物防疫員的工作情況進行檢查考核,對村級動物防疫的工作開展綜合評價,并將評價結果與報酬補貼掛鉤。堅持防疫人員的動態管理,對綜合考評不合格的,要及時調整出村級動物防疫員隊伍;鎮政府與防檢站簽訂動物防疫工作責任書,明確各自職責分工,防控任務逐級分解。各村委要充分認識到自己肩負的防疫工作責任,切實抓好防疫工作的宣傳發動、組織推動和督促落實工作,鎮農業中心和防檢站要認真抓好防疫工作的計劃制訂、技術培訓、疫苗供應和免疫注射工作,形成行政、業務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把動物防疫這項社會性公益事業辦實抓好。
(三)認真落實動物免疫標識制度
各村要扎實做好動物集中免疫注射工作,按照“保證密度,應免盡免”的要求,堅持集中免疫和月月補防相結合,切實做好免疫注射工作,建立完善動物免疫標識制度、免疫登記制度,確保不漏一畜一禽。動物免疫注射后,實行一畜一標,逐戶登記造冊,對農村散養母豬及時進行孕前、產前防疫和仔豬窩防,對新購仔畜及時進行補免,建立免疫養殖檔案,規范動物養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