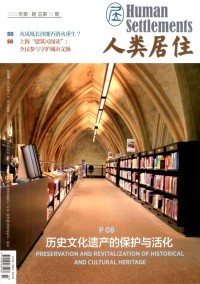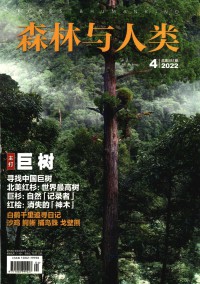人類健康風險評估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第1篇
【關鍵詞】檢驗檢疫 有害生物 集裝箱 風險評估
一、前言
先進的交通工具、現代國際貿易和交流,為外來有害生物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有害生物突破地域限制,引起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外來有害生物對生態系統或物種構成不同程度的威脅,可引起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下降,甚至是物種的滅絕。外來有害生物的范圍很廣,可以是植物、動物或其他各種有機體;且這一范圍正隨著交通運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而不斷拓寬。
二、外來有害生物危害
外來有害生物是指由于人為或自然因素被引入新生態環境,并對新生態系統、物種及人類健康帶來威脅的外來物種。它威脅本地的生物多樣性,引起物種的消失和滅絕,破壞生態系統功能。外來物種通過種種渠道傳入我國,并且已有數百種外來有害生物在我國定殖,給我國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危害。外來有害生物給生態環境、農業生產、人類健康帶來的影響和造成的經濟損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三、進行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重要性
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是評價其傳入(包括進入、定殖)和擴散的可能性、潛在的經濟和環境影響等各項指標的風險大小,對傳入過程中的不確定事件進行識別、預測、處理,使各種風險減小到最低程度的評價措施。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是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陸路口岸集裝箱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既是了解進出境集裝箱攜帶有害生物可能產生的危險性水平,以及這一危險性水平是否可以被接受,并根據需要為降低這一危險性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達到降低外來有害生物傳入風險的目的。
陸路口岸檢驗檢疫機構通過對入出境集裝箱實施檢疫查驗,截獲雜草、昆蟲、病原菌、軟體動物等外來有害生物,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名錄》內列出的檢疫性有害生物,還有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以及具有潛在重要性的有害生物。但是,檢驗檢疫機構人員、技術在現有的檢疫查驗機制下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業務需求,因此,對陸路口岸集裝箱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為植物檢疫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已成為檢驗檢疫部門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四、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方法
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指導性原則和標準還處于早期發展階段,風險評估方法還有一定的不足之處,迫切需要建立科學合理、可行性強、準確性高的風險識別、評估方法對外來有害生物的入侵風險進行預測。
應用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方法,將定性與定量評估相結合,應用計算機軟件和建立各種評估模型作為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的有效手段,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陸路口岸集裝箱截獲有害生物數據收集分析階段
將近年來陸路口岸檢驗檢疫機構在入出境集裝箱中截獲有害生物的數據進行匯總分析。一是將有害生物按照名稱、分類地位、形態描述、啟運國家或地區等信息進行歸類;二是確定有害生物濟環保重要性,判斷其是限定的有害生物還是非限定的有害生物,如為限定的有害生物再區分為檢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
(二)建立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相關因素指標體系階段
根據數據分析結果,以有害生物經濟環保重要性為依據,按照啟運國家或地區、感染情況、季節更替、有害生物狀態、傳入風險、定殖風險、擴散風險、潛在經濟重要性等確定評估因素,然后確定每個評估因素的標準,并確定各因素的權重,每個具體指標可以劃分為多個等級,確定所有指標后即形成陸路口岸檢疫查驗相關因素的指標體系。
(三)建立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階段
根據對陸路口岸集裝箱截獲有害生物相關評估因素綜合評價結果,按照一定規則對各個評估因素的評價值進行綜合評估得出最終評價,進行綜合評價的規則,可以是各種數理統計方法(算術平均、集合平均、取極值、取眾數等),建立起陸路口岸運輸工具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
五、結語
通過在陸路口岸開展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的研究工作,解決當前對集裝箱檢疫查驗過程中人員和業務量迅猛增長之間的不平衡問題,在對集裝箱實施檢疫查驗時突出重點,并滿足現代物流對陸路口岸進出境貨物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要求,同時降低外來有害生物,特別是檢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傳入及擴散的風險,將定性與定量評估相結合,在陸路口岸建立科學的、系統的、操作性強的運輸工具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評估手段,預測外來有害生物入侵風險的大小。
參考文獻
[1]王春林.植物檢疫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
[2]楊昌舉,宋國軍,胡潔品.技術性貿易壁壘――歐盟經驗對中國的啟示[M].法律出版社,2003.
[3]徐海根,王健民,強勝.生物多樣性公約[J].熱點研究:外來物種入侵、生物安全、遺傳資源,2004.
[4]趙月琴,盧劍波.浙江省主要外來入侵種的現狀及控制對策分析[J].科技通報,2007(04).
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多邊貿易體制 公共健康 《SPS協議》 歐共體荷爾蒙案 證據與風險評估原則
Abstract: Free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are both essential to the welfare of human being.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mbraced the subject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ompared with Art.20(b) of GATT1947,the ‘SPS Agreement' balanced, with the help of dispute settlement reg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more reasonably. It is implied in the relevant case study that the Members’ public health sovereignty are being emphasized.
Keywords: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ubic health; ‘SPS agreement'; beef hormones cas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principle
所有學派的學家都確信,自由貿易要比貿易保護好。自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批評重商主義開始,貿易保護由于對一國經濟造成高成本而一直受到經濟學家的抵制。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序言中概括了自由貿易的基礎,即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將會有利于國際分工的,促進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有好處。然而,正如經濟史學家保羅巴洛克(Paul Bairoch)指出的那樣,當自由主義理論統治著學術界的時候,現實主義理論在領域居于支配地位,貿易限制一直是世界經濟的普遍特征。[①]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推重商主義的。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即便是亞當斯密也承認他的關于各國間自由貿易的價值觀存在著一些例外。在某些情況下,各國會追求并非是實現物質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比如說分配正義、反壟斷、資源的保存,以及本國國民的生命與健康安全的保護等等。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討多邊貿易體制下的自由貿易理念與人類健康安全之間的關系演進。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首先來回眸人類貿易史中的若干片斷。
Ⅰ 回顧-------貿易與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控制
如何協調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實際上,作為人類最早用來與傳染性疾病進行斗爭的武器,“隔離”(Quarantine)[②]措施的產生與發展就與貿易直接相關。早在15世紀意大利城邦時期,來自黑死病疫區的商船在到達繁華的威尼斯港口時,都會被要求到一個孤地拋錨停留40天,以避免傳染性疾病的擴散與傳播。[③]以此為發端,到19世紀時各國已經在國內立法中對“隔離”措施建立了一套嚴格而又各異的規范體系。國際層面,自1851年在巴黎召開的首屆國際衛生會議后,歐洲各國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締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拘束力的國際衛生條約(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 1892),以后的國際衛生會議對這一條約又多次進行了修改與補充。這些會議與條約的根本目標可以概括為:一保護歐洲免受外來傳染性疾病的入侵;二 建立針對傳染性疾病的國際監控體系;三 建立國際衛生組織;四 協調統一各國的隔離措施以便利國際貿易的進行。 [④]國際貿易與傳染性疾病在19世紀時就以國際立法的形式緊密地聯系起來,一方面各國有權采取措施保護國內公共衛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須進行國際合作以確保此類措施不對貿易增加不合理的負擔,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在整個國際貿易法的發展史中,這一矛盾貫穿始終。對此,1929年簽訂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CPP)可以作為一個極好的例證。公約一方面承認每一成員國有權利檢查與處置被隔離的進口植物或植物制品,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暫時禁止此類植物或植物制品的進口,[⑤]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員國“除非在某一國家的特定區域確實已經發現了植物病情或蟲害,而且對于保護本國的植物及農作物來說是必要的情況下,不得以植物衛生為理由對該國的植物或植物制品實施進口與運輸限制。”[⑥]
的回顧告訴我們,在20世紀,人類平衡貿易與健康關系的努力更多地是在構建和完善以GATT---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Ⅱ GATT---WTO協調貿易與健康的立法與實踐
一 初步嘗試——《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0條(一般例外)
(一) 《關貿總協定》第20條(一般例外)解讀
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GATT)成立于1947年,當時由23個國家簽訂此協定,其目的在于努力推行貿易自由主義,避免盛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以及貿易戰在戰后重現。非歧視原則是GATT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則,也是GATT作為一個多邊貿易體制得以存在并在戰后國際貿易中發揮其職能的基石。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的多邊貿易協定,在GATT對貿易的規范中同樣包含了對公共健康的關注。透過 GATT第20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多邊貿易體制的設計者們試圖在保證政府的“健康福利權”與防止此種權力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的努力。[⑦]正如杰克遜教授對“一般例外”條款所作的那樣,第20條“承認了主權國家的重要性”[⑧],即成員方政府能夠采取行動以促進‘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其他合法目標的實現,“盡管這種行為會與它在國際貿易中的各種義務相沖突”;[⑨]對政府“健康福利權”的規制以避免其被濫用則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即有關措施的實施:1 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視;2 不得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3 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⑩]
1 對GATT第20條前言的理解
以上1、2兩項體現在GATT第20 條的前言當中,杰克遜教授稱之為“較軟的”(soft)最惠國與國民待遇義務。即在實現第20條所列的目標范圍內,允許偏離第一條(最惠國待遇)和第三條(國民待遇)義務——而不是擴大違反最惠國待遇的歧視性做法,或者是保護國內生產——,如果這種偏離對于追求所列目標是必需的。[11]在1982年的加拿大和美國金槍魚案中,加拿大認為美國對其金槍魚制品的進口限制屬于一種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視,違反了GATT 第20條的規定。專家組裁定,因為美國對其他國家同樣實施了此項措施,因此不能被認定為是對加拿大金槍魚制品不合理歧視。[12]在這里,評估一項措施是否為“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視”的關鍵是看有關的公共健康措施是否是對所有的同類進口產品統一地實施。同樣的,判斷一項措施是否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標準則是看此項措施是否同樣實施于本國同類產品。在“汽油標準案”中誕生了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行以來的第一份上訴復審報告,其中包含了對于“變相限制”一詞的解釋,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上訴機構對于GATT第20條前言的理解——“隱藏的或未公布的對于國際貿易的限制或歧視并未窮盡‘變相限制’一詞的含義。盡管該詞還包含著其他的含義,我們認為‘變相限制’可以被恰當的解釋為包含了在第20條所列一般例外掩護下的國際貿易中達到了任意與不合理的歧視程度的各種限制性措施。……根本性的目標在于防止對第20條一般例外的濫用或非法適用。”[13]
2“必要性要求”的實證分析
前述第3項要求則規定在GATT第20條(b)款本身當中。在GATT—WTO 的爭端解決實踐中,對于“必要性要求”的解釋涉及到了三個問題,其一,當成員方引用第20條(b)款時,相關的措施是否屬于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目的而實施,即GATT第20條對特定案件的“可適用性”問題。 例如,在“泰國限制香煙進口案”中,專家組采納了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吸煙的健康危害性的專家證明,認定泰國對進口香煙的限制屬于GATT第20條(b)款規定的范圍;[14]其二,有關的措施是否是以域外管轄的方式實施。在“金槍魚——海豚案”中,美國認為它所實施的《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MPA)目的在于保護海豚的生命與健康,因此應屬于GATT第20條(b)款規定的范圍。專家組則裁定MMPA試圖將美國的環保標準強加于其他國家,而在GATT體制下這類域外管轄是不被允許的。專家組強調:第20條(b)款允許成員方設立各自的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措施并不意味著成員方可以通過貿易限制的手段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保護標準與健康政策;[15]最后一個問題則是有關的措施是否是為保護健康所必要的(Necessary)。按照GATT—WTO爭端解決專家組的闡釋,“必要”一詞在這里有著確定的含義:如果存在著一個可以達到相同目的的替代措施,并且此項措施符合,或者與所采取的措施相比至少更加不違反GATT義務,那末所采取的措施就不能被認為是“必要的”。[16]同樣是在“泰國限制香煙進口案”中,專家組認為泰國政府本來可以使用其他符合GATT規則的措施,例如“一項在第3 條第4款所規定的國民待遇基礎上實施的非歧視性的法規,要求對香煙的成分進行完全的披露,以及對有害成分加以禁止等等”,[17]來達到減少香煙消費的目的,因此裁定泰國限制香煙進口的做法并不符合第20條(b) 款有關“必要性”的要求。一個相反的例證則是加拿大和法國的“石棉”糾紛。在此案中,專家組指出,法國采取的有關措施屬于保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措施,而且這個措施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可合理利用的替代措施”。[18]
(二)《關貿總協定》第20條(b)款評析
關貿總協定運行以來近40年的表明,第20條的健康例外條款并未達到當初所預想的效果。關貿總協定《GATT與實踐指南》中記錄的以下案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GATT第20條的不足與缺失。
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的核泄漏事故后,歐共體停止了對核電站周圍1000英里以內區域的肉類及活體動物的進口,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成為此項禁令的最大受害者。[19] 匈牙利認為歐共體的做法違反了總協定第20條序言的規定,并認為禁止東歐國家相關產品的進口并沒有基于公共健康安全及方面的充足理由。歐共體對此的解釋則是:在事故之后民眾中存在著非理智的、相互傳播的恐懼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這一措施來平息恐慌。[20]換句話說,歐共體承認了這一禁令從科學及公共健康的角度來說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引發了一個:成員方在援引第20條時,是否必須證明所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事實上,第20條(b) 款并未提及科學證明要求,在GATT解決爭端的實踐中專家組也從未就科學在第20條(b) 款中的地位進行過闡述。
另外一個案例發生在智利,1989年智利的水果出口在一些國家受阻,起因卻只是因為發現了恐怖分子的一次破壞事件導致的“兩顆有毒葡萄”,而這兩顆葡萄卻使智利的水果出口幾乎陷于停頓狀態。智利就此向GATT發出呼吁,敦促成員方更好地協調每一成員方保護其消費者健康的權利與出口國對穩定的和不受限制的國際貿易的期望之間的關系,以避免此類措施由于未經協商而過急實施,由此產生非對稱性(disproportionate)的后果.[21] 這里,我們看到了對第20條(b) 款試圖達到的貿易與健康之間平衡關系的一種期盼,而這種“非對稱性的”后果的產生則與有關措施的科學證明要求以及風險評估程序的缺乏直接相關。如上所述,在第20條(b) 款中既無科學證明要求,也沒有規定對有關情況進行科學地評估以采取適當的、恰如其分的措施。
從以上的可以得出,雖然在GATT第20條規定的一般例外中包含了公共健康安全的,但是在關貿總協定建立之初,其宗旨更在于促進貿易自由化,由于歷史條件和人們的認識所限,貿易與健康之間的平衡關系并沒有被賦予特殊的地位[22] ;GATT并未試圖協調各成員方的公共健康措施,而是允許成員方選擇對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保護標準,前提則是這些措施同樣的適用于相同的進口產品及本國產品,并盡可能對國際貿易產生最小限制作用。然而,第20條條文規定的寬泛和疏漏,特別是缺乏有關的科學證明和風險評估要求,以及由此引發的條文解釋的分歧,一方面使得總協定在爭端解決實踐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另一方面成員方也很難利用第20條為其健康安全措施辯護[23]。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全球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公共健康安全成為各國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如何有效地協調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成為人類面臨的一大難題。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烏拉圭回合產生的《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二 新的路徑——《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SPS協議》)
(一)《SPS協議》概述
《SPS協議》對“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所下的定義對GATT第20 條(b)款中所說的“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作了詳盡的闡釋,根據《SPS協議》附件A, 所謂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是指用于下列目的的任何措施:1、保護成員領土內的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蟲害、病害、帶病有機體或治病有機體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風險;2、保護成員領土內的人類活動物的生命或健康免受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劑、污染物、毒素或治病有機體所產生的風險;3、保護成員領土內的人類的生命或健康免受動物、職務或動植物產品攜帶的病害,或蟲害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風險;或4、防止或控制成員領土內因蟲害的傳入、定居或傳播所產生的其他損害。[24]
按照WTO的理解,《SPS協議》的根本目標是“在確認任何政府提供它所認為適當的健康保護水平的主權權利的同時,保證這種主權權利不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以及對國際貿易產生不必要的阻礙”。[25]為了達到這個目標,《SPS協議》引入了證明原則,規定任何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根據科學原理(based on scientific principles),僅在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內實施, 不在情形相同或相同的成員之間構成任意(arbitrary) 或不合理(unjustifiable) 的歧視,其實施方式不得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disguised restriction);同時輔以風險評估原則,要求成員方保證其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以對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所進行的、適合有關情況的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為基礎[26]。并在第三條中規定了“協調”(harmonization)原則,即除非協議另有規定,SPS措施應根據現有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制定;這些規定的具體含義及其相互間的復雜關系,將在下文中結合有關案例進行詳細評析。
(二) 舉證責任的承擔
“科學證明原則”的引入使得與《SPS協議》相關的糾紛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專業技術,舉證責任的確定也就變得更為復雜和重要。例如,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WTO爭端解決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于舉證責任承擔就給出了相反的意見。
歐共體荷爾蒙案的案情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前,歐共體頒布了三個指令,禁止為促進牲畜的生長而使用含有促進荷爾蒙生長或激素作用的物質,同時禁止將使用前述物質的國產和進口牛肉或肉類產品投放歐盟市場。1997年7月1日,歐盟頒布了新的指令第96/22/EC號,取代前述指令,繼續禁止進口或向歐盟市場投放含有荷爾蒙或激素的肉類或肉類產品,但用于或動物技術的此類物質除外。歐共體荷爾蒙案涉及六種荷爾蒙,其中三種是天然的,另外三種是人工合成的。美國指控歐盟禁止進口含該六種荷爾蒙的牛肉和肉類產品違反了《SPS協議》第2條、第3條和第5條,《TBT協議》和關貿總協定第1條和第2條。
在此案中,歐共體認為應由美國證明使用有關促進生長的激素對人類的健康來說是安全和沒有風險的,[27]而美國則認為應由歐共體來證明健康風險的存在并對此進行科學的風險評估。[28]專家組的意見是,實施有關衛生措施的成員方應承擔舉證責任,在有關的措施高于國際保護標準時更應如此。申訴方只需做出其他成員方違反《SPS協議》的初步(prima-facie)證明, 這之后舉證責任就轉移到了實施措施的成員方那里。專家組認為協議的第2條第2款和第3款、第5條第1款、第6款和第8款、第3 條第2款都支持這一觀點。[29]然而,上訴機構卻推翻了專家小組的結論。上訴機構認為,協議第2條第2款規定實施衛生措施的成員方必須保證“措施的實施僅在為保護人類、動物和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必要限度內實施”,這與爭端解決過程中的舉證責任并無聯系,一個成員方在實施衛生措施時不遵守國際標準的行為并不能導致它必須承擔普遍的或特殊的舉證責任的后果,這樣做實際上是對成員方的一種懲罰。上訴機構認為《SPS協議》下的舉證責任不同于GATT第20條中的舉證責任,專家組本來應當美國和加拿大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證據和論點,證明歐共體沒有遵守《SPS協議》的規定。這意味著美國和加拿大必須做出初步證據,證明歐共體的措施沒有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之上,從而違反了協議第5條第一款的規定。[30]
上訴機構對于舉證責任的認定引發了一個重要后果,那就是在WTO 體制下成員方對SPS措施提出申訴的難度將要比關貿總協定時期大為增加,因為申訴方在案件開始時就必須承擔重要的或者說實質性的舉證責任。結合上訴機構關于任何對違反GATT第20條(b)款的指控必須按照《SPS協議》的規定來解決的主張,我們可以得出,歐共體荷爾蒙案上訴機構的結論對于GATT時期認定舉證責任的標準作出了根本性的變更。在WTO 的實踐中,至少在舉證責任這個問題上,貿易與健康的天平正在向維護成員方的公共衛生安全主權的方向上傾斜。
(二)證據原則與風險評估要求
前述匈牙利肉類及智利水果出口案使我們認識到了GATT第20條的重大局限,有鑒于此,《SPS協議》在第2條第2款及第5條第1款中明確規定了科學證據原則和風險評估要求,它們也被公認為是《SPS協議》的核心條款。
在WTO的爭端解決實踐中,對第2條第2款及第5條第1款的解釋主要涉及到了以下:1 如何構成一項“充分的風險評估”? 2 為證明一項SPS措施符合協議的要求,需要多少科學證據的支持?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這兩個問題都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1 何為充分的“風險評估”?
在該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雖然都認定歐共體的做法沒有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31],但是二者對于“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一詞的含義卻做出了不同的闡釋。
專家組認為風險評估要求包含了程序的和實質的兩個方面,程序方面的要求是指實施衛生措施的成員方必須證明它至少在決定采取措施時“認真考慮到了”(take into account) 有關風險評估的資料,以此來達到該措施是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的要求”;[32]實質方面,專家組認為風險評估要求應包含兩個步驟:(1)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即目的在于發現潛在的人類健康風險的純粹的科學實驗;(2)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包含了成員方希望怎樣去設定適當的健康保護標準的及價值判斷。[33]
然而,對于專家組的上述結論,上訴機構卻給出了相反的意見。首先,對于程序方面,上訴機構認為專家組犯了一個上的錯誤,認為在協議的條文中并沒有包含對成員方證明其在實施衛生措施時就已經考慮到了風險評估的要求,實際上上訴機構并不拒絕一個可能支持有關衛生措施的科學證據,即使成員方從未考慮到這一證據,甚至這一證據是在成員方已經實施了有關的衛生措施之后才出現的;[34]對于實質方面,上訴機構也不同意專家組將風險評估劃分為“科學上的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兩個方面的做法,認為這種劃分并“沒有文本上的根據”(has no textual basis)[35] 上訴機構認為,第5條第1款實際上是對第2條第2款中規定的科學證明要求的一個具體體現,以確保一項衛生措施不是在沒有充分的科學證據支持下實施的。因此,上訴機構澄清,第5條第1款是一個實質性的而非程序性的要求,成員方不僅要能夠舉出對它所實施的衛生措施進行的風險評估,而且必須證明有關措施是被這一風險評估所“充分支持或合理保證的”(sufficiently supported or reasonable warranted)。上訴機構必須查明成員方是否達到了這一要求。[36] 此外,上訴機構主張,“所要評估的風險…并不僅僅是可以在嚴格控制條件下的科學實驗過程中被確定的風險,而且包含了人類社會中實際存在的風險,換句話說,包含了在人類生活、工作、消亡的真實世界里,對人類健康存在的真實的、潛在的負面。[37]對此,有學者評論說,上訴機構對“風險評估”所下的定義“將風險評估從專家組狹隘的、純粹科學過程的定義中拓寬出來”,這種對“風險評估”所作的廣義解釋“為公共衛生當局創造了更大的靈活性,因為‘風險評估’將可能檢測和評估對于人類健康的所有風險,而不問其確切的和即時的起源如何。”[38]
2“風險”及“科學證據”有無量化要求?
在這個問題上,上訴機構又一次推翻了專家組的結論。專家組認為,對一項風險所進行的評估如果要符合第5條第1款的要求,那末該風險的程度應該有一個“門檻”(threshold)的要求,或者說一個量化的要求。[39] 換句話說,風險評估的結果必須體現出一定量級的(magnitude)風險的存在。[40]上訴機構則認為《SPS協議》中并未包含此種要求。按照上訴機構的解釋,成員方只須評估出一種風險,無論此種風險是多末的小,也不論它的可能性如何,只要有關衛生措施與風險評估存在著一種合理的關系,成員方即為履行了風險評估的義務。[41]
上訴機構對風險評估的理解則與它對“少數意見”的態度有關”,這也是上訴機構的結論中最富有爭議的一部分。[42]上訴機構認為,風險評估并不一定非要體現相關科學領域的多數意見,而是可以體現一個有著合格的、令人放心的(qualified and respected )來源的,與多數意見不同的“分歧”(pergent)觀點。[43]這就意味著一個建立在少數科學觀點上的風險評估就可以使相關的衛生措施滿足《SPS協議》的科學證明要求。很多人認為上訴機構的這種結論是對第2條科學證明要求的一大削弱,導致成員方不會遇到太多的困難就可以進行風險評估來支持所實施的衛生措施,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科學家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從貿易與健康安全關系的角度出發,這就證明了科學證據要求并不會對成員方限制貿易以保護公共健康安全的權利產生過多的限制。
然而,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同樣明確了,根據《SPS協議》和《關于爭端解決程規則與程序的諒解》,[44]他們有權對實施有關衛生措施的科學證據的充分性進行判斷。[45]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認為成員方將衛生措施的實施建立在“少數科學意見”上的權利是沒有限制的,成員方必須在爭端解決過程中為其實施的措施提供有效的辯護。
通過對科學證明原則和風險評估要求的,我們可以不難發現,貿易與健康安全之間的微妙平衡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維護。
(三) 協調原則
《SPS協議》第3條(Harmonization)要求成員方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根據現有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制定,以此在盡可能廣泛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協調(第1款);符合國際標準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被視為《SPS協議》和GATT1994的規定相一致(第2款);如果存在科學理由,各成員可采用高于國際標準水平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第3款)。這里所說的“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主要是指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獸疫組織以及《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制定的有關衛生與植物衛生方面的標準指南或建議。
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SPS協議》第3條的解釋又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專家組認為,第3款是對第1款和第2款所規定的,在國際標準基礎上協調衛生措施的一般性義務的一種“例外”[46];第1款中的“根據”(based on)和第2款中的“符合”(conform to) 是同一種含義。[47]上訴機構則明確,第3條的第1款、第2款和第3款各自規定了成員方在實施衛生措施時的權利,第3款中所規定的成員方自行決定衛生措施的保護水平,是一項重要的獨立(autonomous)權利,而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因此,成員方在建立更高的衛生保護水平時,如果未滿足第3款所規定的條件也并不是對第1款的一種事實上的(ipso facto)違反。[48]正是基于以上認識,上訴機構對第3條前三款的含義及相互關系做出自己的闡釋。
上訴機構認為,第1款里要求成員方的衛生措施“根據”(based on)國際標準制定,這里“根據”(based on)的含義是指“在……基礎之上制定”(built upon)或“被…所支持”(supported by)。[49]一項衛生措施如果僅僅是“根據”(based on)國際標準制定,并不等于是與國際標準相“符合”(conform to)。成員方并不能由此援引第2款的規定,認為該措施與“SPS協議和GATT1994的規定相一致”。按照上訴機構的理解,“符合”(conform to)是指“完全地體現了”(embody completely)或者“轉化為國內標準”(convert…into…municipal standard)。[50]一旦成員方選擇了與國際標準不同的保護水平時,第3條第3款就開始獨立地發揮作用。
根據第3款的規定,成員方采取與國際標準不同的衛生措施時,不得與SPS協議的任何其他規定相沖突。上訴機構澄清,這一規定意味著所有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必須符合第5條,特別是要滿足第5條第1款和第2款所規定的風險評估要求。這就意味著,如果成員方選擇了比國際標準更高保護水平的衛生措施,這種措施也必須建立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之上。然而,這一結論又明顯地與第3條第3款的表述相沖突,因為第3條第3款似乎暗示了某些有著“科學理由”(scientific justification)的衛生措施并不需要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之上。對此,上訴機構也承認,SPS協議第3條第3款“‘循環和重疊(involved and layered)的語言’實際上使我們無法做出選擇”。[51]
在筆者看來,這種“循環和重疊語言”的出現更多地體現了協議的制定者們在平衡貿易與健康的關系時的謹慎與小心。
(四)“預防原則”
《SPS協議》的設計者們平衡貿易與健康的努力在第5條第7款、第3條第3款及前言第6段中同樣得到了體現,這些條款在相關的爭端解決中被統稱為“預防原則”(Precaution Principle)。[52]
在歐共體荷爾蒙案中,歐共體主張“預防原則”屬于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并以此證明它的衛生措施符合風險評估的要求。雖然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于“預防原則”在國際法中的地位都未給予明確回答,但二者都確認在第5條第7款和第3條第3款中包含了預防原則的。但是,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都認為,歐共體并不能援引預防原則來規避第5條第1款規定的將衛生措施建立在風險評估之上的明確義務。[53]在日本限制農產品進口案中,[54]預防原則的運用則與第2條第2款的規定聯系起來。在此案中,日本援引第5條第7款試圖證明其檢疫措施滿足了第2條第2款所規定的“充分證據”要求。日本認為,它之所以暫時禁止所有品種的水果進口,是因為缺乏分別測試導致了“相關科學證據的不充足”。對日本的這一抗辯,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并沒有從第5條第7款的實質方面做出判斷,(例如確定在何種情況下,相關的科學信息可以被看作是不充足的),而是著眼于第5條第7款中所規定的程序要求。上訴機構認為,日本既未設法獲得風險評估所需的“額外信息”,也沒有在“一段合理期限內審議”有關的檢疫措施,所以日本的做法并不符合第5條第7款的要求。因此,上訴機構得出的結論,日本的檢疫措施并沒有充足的科學證據,從而違反了第2條第2款的規定。[55]
以上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與歐共體荷爾蒙案和日本限制農產品進口案的似乎表明,《SPS協議》中的預防原則作為實施措施一方的一項抗辯理由,其前景并不令人看好。[56]
(五)小結
綜上所述,從協調貿易與健康間關系的宏觀角度考察,《SPS協議》繼承了GATT第20條有關“必要性”及“對貿易最小限制和禁止變相限制”的要求,并在以下三個方面超越了GATT第20條的規定。首先,協議要求所有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必須建立在科學原則和證據之上,并規定了相關的風險評估程序。這一規定具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有學者認為它使整個多邊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活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課題[57];其次,協議要求成員方應盡可能地在食品法典委員會、國際獸疫組織、《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等國際組織所制定的有關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協調各自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58];最后,作為“烏拉圭回合”一攬子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SPS協議》的誕生使得與健康安全有關的貿易爭議的解決有了強制性的WTO 爭端解決機制作為后盾,這在所有的旨在協調貿易與公共衛生安全之間關系的國際協定中還是第一次。這種超越不僅增加了《SPS協議》的可操作性,而且更為合理地平衡了貿易與健康安全之間的關系。
在與《SPS協議》有關的WTO爭端解決實踐中,有一種現象的出現耐人尋味。那就是專家組,特別是上訴機構只有在有關的案情特別清楚的情況下才會對被訴方是否違反了《SPS協議》相關條款做出明確的結論。[59]這似乎可以被理解為,在通常的情況下,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在權衡貿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時,更傾向于維護一國衛生主管當局保護其本國公共健康安全的權利。
結 語
自由貿易與健康安全同為人類福祉所系。從與傳染性疾病的斗爭開始,直到20世紀以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構建與完善,人類平衡貿易與健康間關系的努力貫穿了整個國際貿易的。我們有理由期待這一努力將會為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帶來更多的和諧與福利。
*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院國際法中心“青年課題基金”的資助,特此致謝。
[①] 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全球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頁。
[②] Quarantine一詞來自拉丁文,意為“40天”,這也是我們在非典危機中耳熟能詳的“隔離”一詞的由來。
[③] See T.Ranger (ed.),‘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1992),p.15.
[④] David P.Fidl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fectious Diseases’(1999),p.2.
[⑤] 1929 ICPP,art 6.
[⑥] Ibid,art 8.
[⑦] GATT1947第20條規定,“在遵守關于此類措施的實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協定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阻止任何締約方采取或實施以下措施……(b)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⑧] John·H·Jackson,‘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97).
[⑨] Ibid
[⑩] GATT1947, art. XX(b).
[11] John·H·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 p 277.
[12] See United States----Prohibition on Imports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from Canada, adopted 22 Feb. 1982,GATT Doc.L/5198,BISD 29S/91
[13]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Appellate Body Report, adopted 20 May 1996,WTO Doc. AB-1996-1,p. 25.
[14] See Thailand---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of and Internal Taxes on Cigarettes, adopted 7 .Nov. 1990,GATT Doc. DS10/R,BISD 37S/200.
[15] Tuna-DolphinⅠCase,para.5.27
[16] See Thai Cigarette Case, Panel Report,para.74; and Gasoline Case Panel Report, para.6.24.
[17] Thai Cigarette Case, para.77
[18]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 Containing Products, WT/DS135/AB, para.150.
[19] GATT ,Guide to GATT Law and Practice ,p.527
[20]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Suspension of Food Imports from Certain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GATT Doc.c/m/198,p. 28.
[21] Establishment of a Streamlined Mechanism for Reconciling the Interest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Event of Trade-Damaging Acts—Communication from Chile, GATT Doc. C/M/ 232, 23, 23-4.
[22] 在GATT第20條中,健康安全只是作為例外之一與其他九項一般例外并列。
[23] 在與第20條(b)款有關的泰國進口香煙案及金槍魚和海豚案里,泰國和美國所采取的措施都被專家組認定為不符合GATT規則。
[24] 參見《SPS協議》附件A。
[25] W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26] 參見《SPS協議》第2條、第5條、第3條。
[27]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50
[28] Ibid, para.8.49
[29] Ibid, para.8.55
[30]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04
[31]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9(i);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253(i)
[32]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113.
[33] Ibid, paras. 8,94,95,160.
[34]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9.
[35] Ibid, para.181.
[36]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6.
[37] Ibid, para.187.
[38] See Fidler, ‘Trade and Health’,p.38.
[39]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188.
[40]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86.
[41] Ibid, para.193.
[42] See Craig Thorn and Marinn Carlson ,‘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 and The Agreement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 Number3, 2000.
[43]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94.
[44] 《關于爭端解決程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11條規定,專家組應對其審議的事項作出“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
[45]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para.192.
[46] Beef Hormones Panel Report,para.8.86
[47] Ibid, para.8.72
[48]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72.
[49] Ibid para.173.,
[50] Ibid.
[51]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74.
[52]《SPS協議》第5條第7款規定,在依據不充分時,成員方在滿足規定的條件下,可以采取臨時性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第3條第3款規定,在有科學依據且措施不違反協議其他規定的前提下,成員方可以采取保護程度高于國際標準的措施。
[53] Beef Hormones Appellate Report, para.124.
[54] 該案的案情是:日本于1950年制定植物保護法和實施條例,禁止從美國等地進口杏仁、櫻桃、梅子、梨、桃、蘋果和胡桃等八種植物。理由是這些植物有可能是幼蛀蟲的寄生體。1978年后,日本有條件的進口以上產品,即只要出口國實施另一可達到進口要求的保護水平的措施,日本便可進口以上植物。1997年,美國要求與日本進行磋商,雙方未達成協議,美國要求爭端解決機構成立專家組審議雙方爭議。
[55] Japan-Varietal Appellate Report, , para.80.
[56] See Craig Thorn and Marinn Carlson ,‘The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 and The Agreement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 31, Number3, 2000.
[57] Charnovitz, ‘Free trade,Fair Trade,Green Trade:Defogging the Debate’, Cornn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7,1994,p480.
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第3篇
【關鍵詞】環境風險;環境風險評價
一、背景
環境風險是指在自然環境中產生的或通過自然傳遞的,對人類健康和幸福產生不利影響同時又具有某些不確定性的危害事件。由于環境風險區別于傳統環境問題,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逐漸發展出一種新的針對環境風險的環境風險評價制度。環境風險評價是指由一定的機關或組織,對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可能對人體健康、生態安全等造成的環境后果進行識別、度量、評估的過程或環境管理活動。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一些法律規范中提出了環境風險評價的內容。1993年,國家環保局頒布的《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規定:對于風險事故,在有必要也有條件時,應進行建設項目的環境風險評價或環境風險分析。同年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要求對基因技術進行安全評價。1996年,《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對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作了規定。2001年,《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指導意見》對職業安全評價作出規定。2004年的《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明確指出:將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納入環境影響評價管理范疇。2011年公布的《外來物種環境風險評估技術導則》規定了外來物種環境風險評估的原則、內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2015年,環保部批準《尾礦庫環境風險評估技術導則(試行)》,要求對運行期間的尾礦庫進行環境風險評估。2014年修訂的新環保法第39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雖然只是國家建立、健全相關制度的義務的概括規定,但同時也使得環境健康風險評價制度第一次進入環保基本法。
二、從一個實踐案例看我國環境風險評價制度的實施
(一)湖北榮成紙業有限公司熱電聯產工程簡介
湖北榮成紙業有限公司擬建設一座熱電聯產中心,為公司生產和和臨港工業園區企業供熱,于2015年6月初通過環評。環評報告的環境風險評價包括五個部分。第1部分為環境風險評價的目的:分析和預測建設項目存在的潛在危險、有害因素、建設項目建設和運行期間可能發生的突發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人為破壞及自然災害),引起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等物質泄漏,所造成的人身安全與環境影響和損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應急與減緩措施,以使建設項目事故率、損失和環境影響達到可接受水平。
第2部分為環境風險評價程序圖,主要包括風險識別、源項分析、后果計算、風險評價、風險可接受水平、風險管理、應急措施預案。第3部分為環境風險評價,報告指出,擬建工程環境風險主要包括:原煤堆場火災風險事故、燃料油火災爆炸、氨水罐泄露、粉塵爆炸、鍋爐故障導致二f英增加外排。以事故發生原因為基礎,將項目環境風險分為火災爆炸、不可抗力、設備故障和人員管理四類。根據相關規定確定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工作等級為二級。對項目的主要環境風險進行分析,主要對每類風險的發生原因進行了介紹,僅對二f英的事故排放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影響進行了簡要介紹。第4部分圍繞原煤堆場火災、油庫、氨水罐、粉塵、鍋爐、事故池、事故廢水處理規定了環境風險事故防范措施。第5部分事故應急反映方案規定了預案的啟動、職責與任務、現場警戒與疏散措施、事故上報程序與內容和善后處理。
另外,根據相關規定,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是作為環境影響評價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所以環境風險評價部分沒有獨立的公眾參與部分,項目環評的公眾參與主要包括兩種方式,一是媒體公示即兩次在湖北省環保廳網站上進行了項目公示;二是公眾參與調查表,對松滋市陳店鎮全心村的83位居民和附近的3家單位進行了問卷調查。公眾參與的結果顯示,當地公眾對建設項目的了解程度一般,部分人擔心項目的運行會對生活環境和身體健康造成不利影響,大部分人認為該項目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解決當地農民的就業問題,被調查者全部支持該項目的建設,無人反對該項目的建設。
(二)分析
從上文介紹的環境風險評價實例可以看出:1、我國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將環境風險僅僅簡要的分為火災、爆炸和泄露三類,并局限在項目的突發性事件或事故可能造成的環境風險,并不對項目正常工作過程中的環境風險進行考量;2、環境影響評價對可能造成的人體健康和生態系統的不利影響的闡述不充分,從而環境影響評價的結論即風險是否達到可接受水平讓人產生不信任感;3、環境風險評價的過程缺乏互動,不能體現評價結論對項目實施方案的具體影響,公眾參與形式化、途徑單一,公眾意見對項目實施缺乏影響力;4、環境風險評價中僅規定了一些事前的預防措施,缺乏事中和事后監督和必要措施。
三、美國環境健康風險管理框架及其啟示
(一)美國環境健康風險管理框架的基本內容
環境風險管理框架已成為國際上環境風險評價制度的發展趨勢,在眾多已制定的環境風險管理框架中,美國總統/國會風險評價和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環境健康風險管理框架》(1997)是最具影響力的框架,為多國制定框架時參考和借鑒。在1990年的清潔空氣法修正案中,國會要求組成一個風險評價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會認為,應改變傳統評價與降低風險的方法,以降低風險和改善健康狀況為總體目標。委員會希望框架指導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有價值的資源投資在研究、評估、表征和降低風險中。
框架包括六個階段:
1.定義問題并把它放在背景下
對科學的風險管理決策而言,首先需要正確界定問題。通過在復雜背景中識別和表征環境健康風險問題并描述它的特征,仔細考慮問題的背景,確定風險管理的目標和有權或有責任采取行動的風險管理者,并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到過程中。
2.聯系問題背景分析風險
闡明問題引起的事實和科學基礎,在數量和質量上處理健康和生態風險,描述負面影響的特性、嚴重性、可逆性或可預防性。把問題引起的風險放在多源頭、多媒介、多種化學物質和多風險背景下。了解利益相關者對問題引起的風險的認識。把問題引起的科學和背景方面的信息結合成問題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產生的風險進行定性,同時考慮利益相關者的認識和其他社會文化的影響。
3.檢查處理風險的選擇
這一階段包括確定可能的風險管理選擇,評價選擇的效果、可行性、成本收益、非計劃中的結果和文化社會影響。這個過程可以在界定問題和考慮背景之后任何合適的時間開始。風險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獲取了關于可行性、成本與效益分析和減少暴露、降低風險對改善人類和生態健康的貢獻的正確評價之后,風險管理目標可能會被重新定義。利益相關者在確定和分析選擇階段發揮重要作用。
4.做出實施何種選擇的決策
在框架的這一階段,決策者基于最佳可得科學、經濟和其它技術信息,確保決策考慮了問題的多種來源、多種媒介、多種化學物質、多種風險背景,做出符合成本收益具有可行性的風險管理選擇。另外,優先預防風險,而不僅僅是控制風險,可能的話,使用命令―控制管理的替代性方案。一個富有成效的利益相關者參與過程可以對決策產生重要指引作用。
5.采取行動來實施決策
傳統上,一直是管理機構的要求推動實施,工廠和市政當局通常是實施者。然而,當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也能扮演重要角色時,成功的可能性會顯著提高。利益相關者可能會包括:公共健康機構、其他公共機構、社區團體、市民、工廠、人和技術專家等。
6.對行動作出評價
在風險管理的這個階段,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評價實施的風險行動以及它們的效果。評價工具包括環境健康監測、研究、疾病監管、成本收益分析和與利益相關者的討論。在大多數情形,應定期評價。就像風險管理過程其他的階段,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讓評價更有益。另外,評價中可能出現新信息,評價對了解框架的哪一部分需要被重復非常重要。
(二)美國環境健康風險管理框架的主要特點與啟示
1.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定義風險
一個風險問題的背景的全面理解對于有效進行風險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問題狹窄的背景無法反映風險情況的真實復雜性,造成風險管理決策和行動相比不是很有成效。
2.基于科學信息和最佳判斷進行風險評價
風險評估者尊重在缺乏充分數據的情況下得到結論時風險和程序的客觀科學基礎非常重要。風險評估者應該向風險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看起來合理的,含有支撐不確定性和供選觀點的具有證明力的評估,從而可以在可得信息的基礎上作出風險結論。
3.利益相關者全過程參與
整個風險管理過程的利益相關方參與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通過全過程參與,不同利益相關方全面溝通與合作,最終平衡各方的意見和觀點以做出體現公眾價值觀的風險決策。
4.重復和評估
公眾評論、協商、信息收集、研究或風險與選擇的分析可能澄清或重新定義問題,使重心改變到一個不同的問題上,由于重要的新信息、觀點和看法出現,風險管理過程會靈活而經常重復。評估對充分地履行職責和理智地利用稀缺資源至關重要。
四、完善建議
(一)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定義環境風險
當前我國環境風險評價制度的規定主要集中在建設項目、外來物種、尾礦庫、基因工程和職業安全領域。其中,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僅適用于涉及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質的項目,排除了有巨大環境風險的核建設項目,而且因為它是以環境風險事故的防范為導向,導致它對環境風險的定義過于狹窄,僅對突發性事件或事故引起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質泄漏進行風險評價,排除了非事故情形下,項目正常運營下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尾礦庫環境風險評估技術導則(試行)》適用于運行期間的尾礦庫,不適用于貯存放射性尾礦、伴有放射性尾礦的尾礦庫環境風險評估,同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它也只考量尾礦庫可能引發突發環境事件的危險因素。《外來物種環境風險評估技術導則》主要適用于規劃和建設項目可能導致的外來物種造成的生態危害的評估。《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和《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指導意見》分別對遺傳工程產品和職業安全風險評估進行了初略的要求性規定。整體來說,從我國環境風險評價的各個分散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環境風險的范圍相對狹窄,而且一般孤立地考慮單一的化學物質在單一的環境媒介中引起的單一風險進行評價,從而也限制了我國全面、綜合的環境風險評價。應改變以事故為導向的環境風險定義,逐步擴大我國環境風險評價范圍,在更廣泛的公共健康和生態背景下進行環境風險評價。
(二)明確環境風險評價的目標
環境風險評價的目標不應停留在防范風險層面上,而應進一步把環境風險評價的目標明確為保障人體健康和生態健康。防范風險雖然是環境風險評價的直觀起點,但忽視人體健康和生態健康目標的環境風險評價是有違環境保護的根本宗旨的。實踐中的環境風險評價正是因為缺乏對人體健康和生態健康的要求而導致實施的結果難以讓人滿意。為了配套環境風險評價保障人體健康和生態健康的目標,國家應積極開展環境健康與環境生態監測、調查與研究,為環境風險評價提供科學和數據支撐。
(三)保障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我國現有的利益相關者參與主要在建設項目(包括尾礦庫)環境風險評價中得到一定的保障,因為環評對公眾參與的要求,公眾在其中可有享有一定的環境知情權、發表環境意見權和環境監督權等,但是,在實踐中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有走過場的傾向,處于弱勢的利益相關方的環境知情權常常受到侵害,意見不能被充分的考慮,對環境風險評價的進程與結論不能產生實質影響。在外來物種、基因工程和職業安全領域,沒有要求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利益相關方的環境知情權也難以得到保障。環境風險是一個多維的概念,還必須包括受影響方的觀點。環境風險評價只有兼顧各方觀點和需求,考慮不同群體的價值觀、知識和認知,才能做出更好的風險管理決策,而在決策行動的過程中也不易受到利益相關者的反對和抵觸。
(四)構建適合我國的環境風險管理框架和方法
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第4篇
由于本案牽涉復雜的技術問題,為此專家組規定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期限,以供各當事方提交科學證據,并專門成立了專家咨詢小組,為案件審理提供技術咨詢。同時,專家組對舉證責任在爭端雙方之間的分配問題作出裁定,先由方美國和加拿大提出初步證據,證明歐盟措施不符合SPS協議的規定,之后舉證責任轉移給歐盟。但在具體審理過程中則更加強調了作為采取SPS措施的一方,即歐盟的舉證責任。
歐盟措施沒有以風險評估為依據
根據SPS協議第3條第1款和第3款規定,一國采取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以國際標準、準則和建議為依據,而如果一國采取高于國際標準保護水平的措施,則需遵守協議第5條各款的規定。為此專家組首先考察歐盟采取的措施是否以國際標準為依據,在得出否定的結論后,專家組就歐盟采取的高于國際標準保護水平的措施是否符合第5條各款的要求進行了重點考察和分析。
SPS協議第5條第1款中包含了一個程序條件,即采取措施的成員方應當證明它至少在決定采取措施時認真考慮了風險評估的資料。在對歐盟提供的證據進行了分析后,專家組認為歐盟沒能滿足這種程序條件,并且其采取的措施雖然被說成是保護人類健康所必需的,但并不是以其提交給專家組的科學證據為依據的。由此專家組得出結論,認為歐盟采取的措施不是根據協議所指的風險評估作出的,違反了SPS協議第5條第1款的規定。
專家組指出雖然設定適當的衛生保護水平是成員國的,但成員國在行使該項權利時需要遵守SPS協定其他條款,尤其是第5條第4款、第5款的規定,即各成員在決定適當的衛生與植物衛生保護水平時,應考慮將對貿易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一目標,并應避免其認為適當的衛生保護水平在不同的情況下存在任意或不合理的差異。專家組并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再根據第5條第6款,進一步審查這些措施是否更具貿易限制性。
最終專家組裁定歐盟的措施沒有以風險評估為依據,其在實施它認為適當的衛生保護水平時,在不同情況下存在任意的或不合理的差異,這種差別構成對國際貿易的歧視或變相限制,歐盟的措施違反了SPS協議第5條第1款、第5款以及第3條第1款的規定。
爭議焦點
上訴機構審理的核心問題是專家組在適用SPS協議有關條款,主要是第3條第1款、第3款以及第5條第1款、第5款上是否存在錯誤,此外還涉及一些需要澄清的適用程序等方面的問題。
對于歐盟的措施是否以國際標準為根據,焦點集中在如何理解“根據”(based on )一詞的含義上。專家組在解釋“根據”一詞時,將“根據”國際標準制定的措施等同于“符合”(conform to)國際標準的措施,進而得出成員國的SPS措施必須符合國際標準的判斷。上訴機構認為,“根據”的普通含義不等于“符合”,而且SPS協定第3條在不同的款項中使用了“根據”和“符合”兩個不同的詞,這更表明其含義不同。此外,第3條的目的和宗旨也不支持專家組的這種解釋。上訴機構在確認專家組所犯錯誤的同時,明確了判斷某項措施是否根據國際標準而制定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該措施所能達到的保護水平。如果國際標準反映了衛生保護的特定水平,而某一項衛生措施暗示著不同的保護水平,那么這項措施就不能被認為是依據國際標準而制定的。
基于協議第3條第3款確定本國適當的衛生保護水平是成員國的一項自利,但成員國在采取高于國際標準衛生保護水平的措施時,有義務遵守第5條第1款的要求。上訴機構認為,對第5條第1款的遵守,是各成員確定其自己適當保護水平權利的一個制約因素。第5條第1款關于風險評估的要求以及第2條第2款“充分的科學證據”的要求,對于維持SPS協議在促進國際貿易與保護人類生命健康之間經過微妙的、細致的談判而達成的平衡是十分必要的。為此上訴機構同意專家組對此問題的結論,即歐盟如果要符合協議第3條第3款的要求,就必須遵守協議第5條第1款的規定。
如何理解“SPS措施以風險評估為依據”
上訴機構首先澄清的問題是:風險評估是否指的是對風險所進行的科學的、定量的分析。上訴機構認為,SPS協議本身并沒有這種規定,也沒有對風險最低量的要求。而協議所要評估的風險,不僅包括通過科學的定量分析才能查明的風險,也包括人類社會實際存在的、對人類健康具有潛在不利影響的風險,評估時不能將無法通過定量分析的事項排除在外。
上訴機構認為“以風險評估為依據”是一種實質性要求,意指SPS措施和風險評估之間應該存在一種合理的關系,即SPS措施需要得到風險評估的合理支持和保證,但這并不意味著風險評估必須得出與科學結論或SPS措施所暗示的觀點一致的獨立的結論,確定合理關系存在與否只能在合理考慮到所有潛在不利影響的問題后,逐案進行分析。
上訴機構分析了專家組對第5條第1款的適用情況,并確認了專家組的最終結論,即歐盟的進口禁令并沒有以SPS協議第5條第1款和第5條第2款意義上的風險評估為依據,不符合第5條第1款的要求。相應地,也不符合SPS協議第3條第3款的要求。
關于第5條第5款,即歐盟是否在實施它認為適當的衛生保護水平時,在不同情況下存在著任意的或不合理的差異,這種差別構成對國際貿易的歧視或變相限制。上訴機構重申了專家組關于違反該條款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并指出其中第二個要素的存在,即不同情況下保護水平的差異是任意的或不合理的,在實踐中可能作為一個“警示”標志使用。隨后上訴機構對專家組的具體適用過程進行了審查,認為專家組對這一問題的裁斷缺乏充分證據支持,因而了專家組對這一問題的結論。
關于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專家組在案件的審理中,強調了對于沒有根據國際標準而采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一方的責任,主張應該由采取措施的一方對措施的合理性承擔證明責任,并免除申訴方在這方面的責任。上訴機構不同意專家組這種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實施SPS措施的成員一方的裁定,提出專家組應首先審查美國和加拿大是否已經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歐盟所采取的措施違反了SPS協議有關條款,只有在專家組確定已構成那樣的初步證據時,舉證責任才轉由歐盟承擔。
本案三大啟示
美國與歐盟就使用荷爾蒙物質的牛肉問題曾發生過長期的貿易摩擦,雖經長時間審理,最終以歐盟敗訴而告終,就SPS協議的適用而言,今后實踐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上訴機構提出以國際標準為根據,并不意味著成員國的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必須與國際標準相符合,完全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根據”國際標準制定的SPS措施的適用范圍,使得國際標準在協調各國SPS措施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范文第5篇
關鍵詞:污染場地;地下水;污染物運移
地下水污染健康風險評估是健康風險評估在地下水環境保護治理領域的衍生概念。基于保護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考慮,以地下水質量標準和風險評估的健康基準值為基礎,客觀、科學地量化評估地下水污染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產生的潛在影響。地下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地下水原有物質進入地下水后可能會對地下水造成污染,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治理和恢復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應用科學有效的方法進行地下水環境影響評價是非常必要的。
一、地下水健康風險評估方法
1、地下水暴露量的計算
該研究在進行場地地下水健康風險計算中主要考慮的暴露路徑為人體直接飲用途徑,運用地下水飲用途徑暴露量計算公式對污染物在場地地下水中的暴露劑量進行計算,可得到地下水飲用途徑污染物暴露劑量。
ADD=(1)
式中,ADD為經口暴露劑量;CW為水中污染物濃度;IR為人的飲水率;EF為暴露頻率;ED為暴露持續時間;BW為人的體重;AT為平均暴露時間。
2、場地地下水健康風險計算
根據石油類污染物對人類的不同毒性特點,可將地下水健康風險分為致癌風險和非致癌風險。致癌風險即對人體造成致癌效應的風險,一般認為沒有劑量閾值,只要有微量存在,即會對人體產生不利影響。根據美國國家環保局(EPA)推薦值可知,當致癌風險值大于10-6時,表示污染物致癌風險超過可接受水平;非致癌風險則指對人體造成非致癌效應的風險,一般認為有劑量閾值,低于閾值則認為不會產生不利于人體健康的影響。當非致癌風險值大于1時,表示污染物非致癌風險超過可接受水平。對于一種污染物質,可能既具有致癌風險,又具有非致癌風險,這時應分別對其計算致癌風險及非致癌風險。
地下水污染物的致癌風險模型計算:
R 1 =ADD×SF(2)
式中,R1為致癌風險(無量綱);SF為致癌斜率因子;ADD為致癌污染物地下水飲用暴露量。其中,當R1值大于10-6時,表示污染物致癌風險超過可接受水平,需要進行修復。
地下水污染物的非致癌風險模型計算:
R2=(3)
式中,R2為非致癌風險(無量綱);RfD為經口攝入污染物參考劑量;ADD為非致癌污染物地下水飲用暴露量。其中,當R2值大于1時,表示污染物非致癌風險超過可接受水平,需要進行修復。
二、實例研究
評價區位于工業園區內,地理坐標為東經119°38'―119°40',北緯45°26’―45°27'。地貌屬山前沖洪積地貌,地形起伏較大。地層上部為第四系沖洪積、風積細砂及沙礫石層,下部為凝灰質膠結的沙礫層。所在含水層為松散巖類孔隙與基巖風化帶孔隙裂隙潛水含水層(組),含水層巖性為含礫粉細砂、礫石、凝灰巖等,厚度25―35m,水位埋深2―5m,導水系數(T)59.81―259.2m2/d,滲透系數(K)3.15―8.64m/d。通過上述分析,模擬評價區的水文地質概念模型可以概劃成非均質、各向同性、二維非穩定流地下水流系統。
1、數學模型的建立
評價范圍內水流狀態符合達西定律,利用有限差分法或有限單元法進行數值求解。本次模擬把包含模擬評價區的矩形區域在二維平面上剖分成125×125=15625個網格單元,其中模擬評價計算區6607個單元,共6個區。
2、模型的識別和驗證
模型的識別與檢驗過程是整個模擬中極為重要的一步,通常要經過反復修改參數和調整某些源匯項的過程才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擬合效果。模型的識別與檢驗過程采用的方法稱為試估――校正法,屬于反求參數法。通過反復調整參數和均衡量,識別水文地質條件,確定模型的結構、參數和均衡要素。最終確定了各個分區的水文地質參數如表1所示。
表 1 模擬評價區含水層參數
識別后的含水層水文地質參數
分區編號 參數值 分區編號 參數值
滲透系數(m/d) 給水度 滲透系數(m/d) 給水度
1 6.8 0.25 4 4.5 0.15
2 4.5 0.15 5 3.5 0.18
3 6 0.2 6 7.5 0.2
3、溶質運移影響因素及模擬時間段的確定
根據污染源特點,本次污染物預測評價過程不考慮污染物在含水層中的吸附、揮發、生物化學反應,只考慮運移過程中的對流、彌散作用。模擬時段確定為自泄漏時間點起30年,共計10950天,設定滲漏時間起點為2011年1月。
4、污染物質的確定
大修渣成分復雜,并非只有一種污染物,而是存在一種主要污染物和多種次要污染物,根據大修渣取樣進行的相關浸出試驗結果,確定大修渣主要污染物為氟,濃度為300mg/L。
5、模擬結果分析
1)非正常工況無防滲措施情景預測
根據評價區污染物濃度大小,對氟污染物進行預測分析,特征污染物氟的污染羽在彌散、對流綜合水動力作用下,逐漸向東南方向遷移出污染場地并向下游運移,污染羽的面積逐漸增加,濃度由于水流的稀釋在逐漸降低。100d后,影響范圍為91721m2,超標范圍64166m2,最大運移距離239.9m,最大超標倍數約93.4倍(對應的濃度為93.4mg/L);1000d后,影響范圍為468101m2,超標范圍243355m2,最大運移距離713.8m,最大超標倍數約17.1倍(對應的濃度為17.1mg/L);10000d后,污染羽的最大濃度為0.12mg/L,遠遠小于限值,所以不存在超標現象,但存在影響范圍,面積為311649m2,預測結果詳見表2。
表 2 地下水中氟污染預測結果
污染年限 影響范圍(m2) 超標范圍(m2) 最大運移距離(m) 最大超標倍數 最大濃度mg/L
100天 91721 64166 239.9 93.4 93.4
1000天 468101 243355 713.8 17.1 17.1
10000天 311649 - 829.4 - 0.12
2)非正常工況有防滲措施情景預測
有防滲措施,污染物僅通過防滲層破損點滲漏,進入地下水的污染物總量急劇減少,濃度將大大少于無防滲措施下的濃度。根據無防滲措施的預測結果來看,在非正常工況采取防滲措施時,下游廠區邊界地下水污染物濃度變化差異顯著,各污染物達到穩定濃度的值遠小于檢測下限。地下水污染程度明顯減弱,均未超出檢測下限。
結論
綜上所述,雖然污染場地砂卵礫石層能對污染物起到一定的吸附和凈化作用,但由于其滲透性很大,在污染物濃度超標很大的情況下不能有效地吸附,超標的污染物會隨地下水向下游運移。在有防滲膜的前提下,污染物的擴散、遷移路徑被有效地阻滯,當污染物擴散至砂卵礫石層及其下部地層時,濃度已明顯減小,水平擴散范圍及侵入深度也明顯減小,因此不會對污染場地下游區域地下水水質產生影響。
參考文獻
[1]王克三。地下水污染及其監測治理問題[J].水文地質工程地質,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