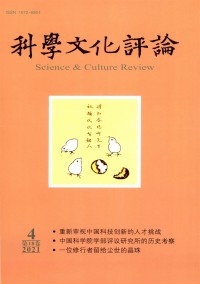科學文化批評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科學文化批評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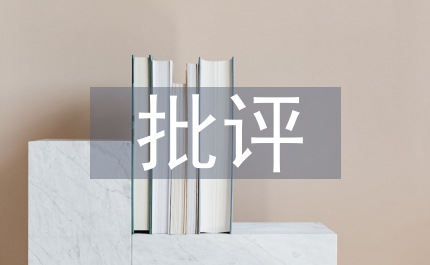
丹皮爾曾說:19世紀是科學的世紀。此話同樣可用于20世紀,因為20世紀仍然可以說是科學的世紀;科學文化是20世紀最顯著的文化現象,科學主義也是20世紀最有現實影響的文化思潮。顯然,在一定時期內,這兩者具有某種互動的關系。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兩者之間具有永恒的必然聯系。本世紀下半葉的事實是,科學文化仍在日新月異地發展,在人類文化領域中顯示了巨大的生命活力,而科學主義卻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包括來自自己陣營內部的批評。科學文化與科學主義思潮顯示了某種分離的趨勢,成為世紀末耐人尋味的一種文化現象。科學向何處去,科學在人類文化領域中究竟如何定位,將成為下個世紀的重大文化課題。從這一角度看,對科學主義批評的研究有著特殊的意義,可以說它是我們現在能夠透視下個世紀人類文化、特別是科學文化走向的重要途徑。
到目前為止,對科學主義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科學主義理論基礎方面,主要集中在科學本身的規定性上,或者說,集中在科學的劃界問題上。這方面的批評首先是從科學主義流派內部開始的。二是集中在科學與人的關系上。這方面的批評來自人文主義思潮,歷史悠久,很有影響。三是來自科學本身的發展。如果說,科學主義的形成受惠于某個階段的科學發展,那么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它的最新內容顯示出來的特性與科學主義的本性就不那么相容了。換言之,科學主義已經受到了來自科學本身的批評。本文且按照這三方面的歸納展開進一步的評述和研究。
一、來自科學主義內部的對科學主義的批評
科學主義首先是將科學塑造成“超級大國”而后再向外擴張的。邏輯經驗主義作為科學主義的成熟形態,首先力圖使科學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而后以此為標準努力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科學本體的絕對存在,或者說,確立科學與非科學劃界的絕對標準,是科學主義的首要任務,也是邏輯經驗主義始終一貫的中心議題。在邏輯經驗主義那里,除了分析命題以外,凡是能為經驗證實或證偽的命題,就是科學的命題。這一訴諸經驗的劃界標準是絕對的、不容置疑的。
然而,從50年代起,這一標準受到了批評。這方面的批評源于科學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主要從科學哲學的內部引發,大體可以以下三種類型的批評為代表。
1、奎因的整體論批評。
邏輯經驗主義認為,一個孤立的命題能被經驗所驗證,通過這種驗證劃分科學與非科學;奎因認為,這是一個做不到的教條。
奎因思想的最早形式見于1906年法國哲學家皮埃爾•杜赫姆。杜赫姆認為不存在所謂能驗證命題真偽的判決性實驗。舉個例子說,假定有這樣一個假設H:一股2安培的電流正在通過一條導線,那么可以預言的實驗結果O:安培計指針指向表盤刻度第2格。即H→O。若有O,則H真;若無O,則H假。這就是所謂的判決性實驗。但是,這樣的判決實際無法做出。因為包含在這一過程中的真正的邏輯關系是:(H、A1、A2……)→O。其中A1可能代表安培計構造原理,A2代表通電導線的電磁原理,A3代表儀器是正常的等等。這樣,即使無O,我們也不能得到H為假的結論。即我們不能證實或證偽H,無法判斷H的科學性。
奎因進一步提出了整體論看法。他認為整個知識體系是一個以經驗為邊界條件的力場。一旦這個體系在其外圍跟經驗發生了沖突,受檢驗的是一個整體而不是某個部分。沖突的結果是導致力場內部的重新調整,真值也就在場中的一些陳述中重新分配。這樣,證實或證偽都成為相對的了,因為“在任何情況下任何陳述都能夠被決定是真的,如果我們在系統的其它部分作出足夠劇烈的調整的話”。力場部分作調整受“革命原則”和“保守原則”指導。“革命原則”主要指“探索的簡易性”;“保守原則”主要指原理的熟悉性。于是,我們是否接受一個假設為真,不再僅僅訴諸經驗,還取決于整體論條件和上述的理論原則。科學與非科學劃界的標準開始模糊,走向相對化。
2、庫恩的范式批評。
庫恩用范式概念進一步使科學劃界標準相對化。他認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僅限于某個范式之中。范式是歷史的,范式與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不存在適用于所有范式的普適的劃界標準。庫恩說,一個范式是科學共同體共同信奉的價值標準的集合,是教科書中反復灌輸的共同方法、準則和基本假設的集合。在這范式之中,根據這些標準共同體判斷什么是科學的,什么是非科學的。如果離開了這一范式而到了另一范式之中,評價標準就發生了變化。為一個范式認為是科學的理論可能為另外范式的共同體所拒斥。因此,范式之間不存在統一的規范標準用以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科學與非科學,只存在某種相對的劃分。
進一步看,盡管范式可以成為科學劃界的相對標準,但由于范式本身包含形而上學的信念和其它社會的、心理的、價值的因素,也就是說標準本身滲入了非科學成分,因而我們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絕對劃清科學與非科學界限的。由于科學被非科學的因素污染,所以,科學崇拜難以成立。
3、費耶阿本德的反規范主義的批評。
費耶阿本德比奎因和庫恩走得更遠,走向了徹底的相對主義。其基本觀點是:“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離不僅是人為的,而且對知識的進展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要理解自然界,如果我們要支配我們的物質環境,那么我們一定要使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方法,而不僅僅使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但關于科學之外無知識的斷定卻不過是另一個最方便的神話故事罷了。”
這就是說,科學與非科學之間不存在絕對界限。天文學得益于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對圓周的喜愛。醫學得益于草藥學、巫婆和江湖醫生的心理學、形而上學與生理學。“科學處處為非科學方法和非科學成果所豐富”。“偉大的科學是不知道有任何界限的,是一種不承認任何規則、甚至包括邏輯規則的理智的冒險。”科學不承認任何規則的普適性。一切方法都有局限性。剩下來的唯一規則是“什么都行”。一切方法都可以放到方法論的工具箱里。“任何解決問題者,并不像一個小孩那樣,要等候方法論爸爸或理性主義爸爸給他提供一些規則。他不依賴任何明顯的規則而行動,并且以他的行動構成合理性,否則科學就從來不會出現,科學革命就從來不會發生。”
費耶阿本德進一步對科學的神圣地位進行挑戰。他認為科學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其地位而言,“科學只是人所發明用以應付他的環境的工具之一。它不是唯一的工具,不是絕對可靠的。”它是“有許多優點但也有許多缺點的一個有趣的但決非唯一的知識形式”。科學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科學與其它意識形態的爭論沒有結束。費耶阿本德在對科學主義的批評過程中已經轉到人文主義的立場。他認為評價科學的標準是:在何種程度上,個人的幸福和自由增加了?按照這一標準衡量,科學有許多缺陷。如把人變成沒有魅力和幽默感的、可憐的、不友好的、自以為是的機械裝置;使人處于緊張忙碌的野蠻狀態,以一種“最新近的最有挑釁性的、最獨斷的宗教制度”的形式出現,通過科學與國家的一體化,推行科學沙文主義等等。
至此,科學主義內部的批評者們走向了科學主義的反面,成為人文主義的同盟者。
二人文主義對科學主義的批評
人文主義對科學主義較早的批評可以盧梭為代表。盧梭在應法國第戎科學院懸獎征文而撰寫的《論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促進了風俗的淳厚》一文中,指責科學和藝術鞏固了專制社會,扼殺了人們固有的自由感情;隨著科學藝術近于完善,人的靈魂被腐化了。科學的創立者敵視人類安寧,它們生于游手好閑,反過來又培養游手好閑。盧梭觀點的重要之處在于,他從反面看待科學的社會作用。這與科學主義觀點是格格不入的。
之后,康德提出“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的命題,以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兩分法論證科學解決不了道德問題,設立了上帝存在、靈魂不死、意志自由的律令,為信仰留下了地盤,觸及了科學全能觀的要害。在此之后,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也向科學全能觀發問:“人們希望科學教給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同家人、鄰居和外國人相處,如何在感情交戰中把握住該相信什么和不該相信什么,以及其它更多的東西。但是,科學把這一切告訴人們了嗎?”尼采在這方面更是前無古人,他代表人文主義對科學全能觀進行了全面討伐。尼采因此成為人文主義現代崛起的主要代表。尼采提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論證科學不是全能的:其一,科學理性存在極限。任何科學體系都不能完全以科學因素而自足,都存在著“命令式的無條件的原理”。科學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它“缺乏愛,也不懂得任何不滿和渴望的深情”。其二,科學理性源于非理性,后者是前者的發生基礎。生命本能是第一位的,理性是派生的,并且是為生命服務的。真理是人用來保存自己的條件和工具。其三,科學認識不可能達到“真正的世界”。實際上,這種理性宣稱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是用一種彼岸的生活向生命復仇。
如果說,尼采已經就科學理性對人的負面影響進行了譴責,那么在他之后,此種聲音不僅不絕于耳,而且屢屢響起。愛因斯坦在二次大戰后指出;“我認為今天人們的倫理之所以淪喪到如此令人恐懼的地步,首先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的機械化和非人性化,這是科學技術思想發展的一個災難性的副產品”。愛因斯坦認為,科學是既能行善也能行惡的雙刃寶劍。科學不能提供目標,只能提供手段、方法。羅素也對人的科學性解釋指責說;“人竟是毫無準備的因果產物,他的起源、他的希望和恐懼,他的愛和他的信仰竟然只是原子偶然搭配的結果,競沒有熱情,沒有英雄氣概,沒有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這怎能不使人的生活墜入野蠻”。當代的法蘭克福學派也在這方面對科學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評。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認為,隨著人對自然控制能力的提高,人類越來越依賴于科學技術,使人的目的和手段倒置,人淪為物——機器的奴仆,成為無感情、無靈魂的工具。因此,人類要努力擺脫邏輯和數學的“專制主義”。馬爾庫塞斷言,理性必然成為統治和奴役人的工具,在科學理性基礎上建立的現代社會是“單向度”的社會,產生的是“單向度”的人。這是社會技術化的后果。
對科學主義非人性化的思想批判已發展為某種群眾性的社會批判。典型的事例是綠色和平運動。這一運動提出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的口號,反對無休止地發展科學技術用以開發能源,消耗資源,牟取暴利;反對把科技無條件地運用于工業生產,以免制造污染,破壞生態平衡。這一運動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以致人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變綠。
三科學本身對科學主義的批評
20世紀以來科學的發展對舊的科學觀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科學主義面臨著困難的處境。在這方面首先對科學主義提出有力挑戰的主要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蘊含的思想與科學主義相悖。正如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把時間、空間、質量、速度視為絕對量一樣,科學主義也是把科學的一部分乃至全體絕對化,使它成為一個不可超越的絕對參照系。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翻了試圖把參照系、主體或客體絕對化的作法。這一理論認為時間、空間、質量等都不是絕對量,而是相對于一定參照系的相對觀測值。愛因斯坦的結論是通過下述過程推出的(簡單表述):
前提1,物理學定律在所有慣性系中是等價的,不存在任何一種特殊的慣性系;
前提2,在所有慣性系中,自由空間中光速具有相同的值C。
由此推出洛倫茲變換式:
(1)式和(2)式的解讀是:相對于不同的參照系,空間量度和時間量度都是不同的(L’<L和Δt’>Δt)。所以,時間、空間都是相對于一定的參照系而言,都是一種相互關系。時空是相對于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而得到的量度,不存在能超越所有參照系的全知全能的認識主體。所有的認識主體必須相對于他的參照系來講話。參照系變了,話語也應改變。按照這一科學理論,絕對參照系與絕對主體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量子物理學得出的基本原理也與科學主義的觀點相矛盾。測不準關系表明,主客體絕對分割,或主體與參照系絕對獨立以求知識絕對客觀化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據這一原理觀察到的量子世界的現象是和測量裝置以及觀測人的作用密切相關的。測量時主體對客體的作用不可避免。所謂科學能夠擺脫認識主體的影響,從而達到純粹客觀真理的看法已為測不準原理所推翻。
測不準原理包括兩個部分:
對于1式,若ΔX=0,則ΔPx=∞;若ΔPX=0,則Δx=∞。即若x精確地測量,則動量Px一無所知,反之亦然。例如,我們試圖精確確定一個“點”粒子的位置,為了看到這一電子,我們必須將它照明,因為觀察者見到的實際是被電子散射的光量子。當我們照明電子時,由于康普頓效應,電子被反沖得不能完全測定。若不照明它,我們又觀察不到它。所以,正是觀察電子這一動作干擾了電子本身。主體發出的動作與客體的性質不可分,兩者之間總存在一種不可確定的相互作用,這就是測量過程中的測不準原理。這一原理肯定了主體的觀察方式對客體性質的影響和作用。
波爾就此發揮提出了互補原理。他提出由于人們的觀察方式不同(注意,這與相對論的參照系意義相同),因而得到的對客體的觀點也不同。不過,這些不同的觀點和語言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補的。經典物理學與量子物理學的語言都是合理的必要的,科學的語言與其它的人和自然之間的對話也都是合理的。這樣,就不同的參照系、不同的觀察方式而言,就有不同的、然而是同樣合理的描述語言。不存在某種絕對的描述語言。按照這種相對化了的互補原理,科學主義對科學自身的絕對期待就完全落空了。
四對科學主義批評所作的簡要評析
本世紀下半葉以來發生的對科學主義思潮的批評,是當代宏觀文化領域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一種文化現象。研究這一文化現象的特殊重要意義在于,通過這一文化現象的評析,可以察究當代文化領域的動態和下一步的走向,引出一些極為重要的看法。
至少有以下幾個要點值得注意:
1、在文化領域中人們對科學的看法與以往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種種跡象表明,科學可能并不像人們所樂觀預期的那樣,是具有終極意義的文化形式;人類有理由對未來新的文化形式作某種展望。
對科學看法的重大改變首先是科學價值觀的改變。對科學主義的批評,火力集中所在也首先是價值領域。中心問題是科學的價值評估,即對科學究競應作什么樣的估價,把它擺在何種位置。科學主義的批評者們對科學的崇拜進行的猛烈的抨擊,導致了科學神圣性的下降。對科學的樂觀主義的牧歌式的評價已逐漸為冷靜的客觀分析所取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仍然得到其它文化形式未曾享有的殊榮,但它同時毫無疑義地顯示了自身非神圣的一面。人類開始注意到科學的局限。
對科學看法的另一改變源于科學的認識論。科學本身的發展愈來愈暴露出科學的相對性的一面。人們對科學的本性有了新的理解。
這些都表明,在科學勝利進軍中人們對科學的過分贊頌顯示了歷史限制性的一面。科學也不是至高無上的。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它也不應是文化形式發展過程的頂峰階段。人們已經開始進行新的探索。例如,胡塞爾強調說:“根本談不上哲學必須把精密科學的方法當作楷模”。“哲學處于一種全新的維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發點以及一種全新的方法,它們使它與任何‘自然’的科學從原則上區別開來”。
2、在文化領域內部,科學與其它文化形式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科學與其它文化形式對立的緊張關系得到緩解;科學與其它文化形式的整合關系已大于以往的分離趨勢;科學與非科學的文化形式之間的界限的模糊性已日益為人們所認識。
在科學誕生之初,科學是中世紀宗教神學的對立面,與宗教神學處于尖銳的斗爭狀態中。之后,科學又以哲學為對手,清算了“形而上學”。科學確定性的理想與藝術非理性的一面也是矛盾的。總之,作為文化領域的新伙伴,它像一個毛頭小伙子,與其它伙伴處于一種緊張對立的分離狀態中。現在,這一情況發生了逆轉。科學與宗教、科學與哲學、科學與藝術都處于某種新的格局中。至少,緊張狀態已告一段落。
3、在文化形式與人的關系方面,重心再次擺向人本身;科學開始找到自己的目的——以人為歸宿;科學也開始意識到人文主義對自身的根本制約,意識到科學作為工具理性應當置于人的需求這一目標之下。人們也開始這樣考慮問題:人類一直存在的對自己所創造的文化形式的崇拜是不是時到今天應當宣告結束?如果是這樣的話,對科學主義所作的批評就有了新的超出這一批評本身范圍的重大意義。
我們是不是應該就此想得更多一些?
注:
亨普爾:《邏輯經驗主義:它的問題和演變》,見《現代外國哲學論集》(二),1982年版,第81—83頁。
見葛力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辭典》,求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頁。
見江天驥,《科學理論的評價問題》,涂紀亮主編:《分析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6—20頁。
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倫敦新左派書社1975年版,第306頁。
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倫敦新左派書社1975年版,第305頁,
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倫敦新左派書社1975年版,第182頁
轉引于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頁。
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倫敦新左派書社1975年版,第217—219頁。
轉引于英里斯•戈蘭:《科學與反科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頁。
尼采:《快樂的知識》,第344節。
見《尼采全集》第1卷,第453頁,第8卷,第81頁。
見《尼采全集》第1卷,第453頁,第8卷,第81頁。
《愛因斯坦談人生》,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頁。
轉引于英里斯•戈蘭:《科學與反科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頁。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R•瑞斯尼克;《相對論和早期量子淪中的基本概念》,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215頁。
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