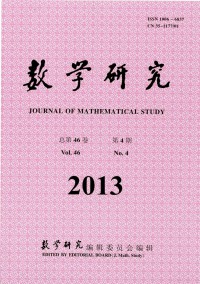數學題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數學題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數學題范文第1篇
可是沒想到妹妹居然這么笨,我告訴她1加1等于2,問她1加1等于幾,妹妹想了想說:“等于10。”我說:“不對重新算一算。”妹妹又想了想說:“等于8。”這不是瞎蒙嗎,真是氣死我了。
我又生氣又喪氣,真是教不會她了。我心里打起退堂鼓,可是又想起答應教會妹妹的,沒教會怎么向媽媽交代呀。不行,我得想個辦法。對了,姐姐教我是叫我用手指頭算的,我也用這個方法教妹妹吧。
“一個手指頭加上兩個手指頭,等于幾個手指頭?”我舉著手問。妹妹數了數說:“等于3。”對了,那1加2等于幾?妹妹數了數手指頭說:“等于3。”我又說:“1加3等于多少?”妹妹說“等于4。”我又說:“2加3等于多少?”妹妹想不出來就數了數手指頭說:“等于5。”我想妹妹真會用手指頭算了。
數學題范文第2篇
這道中國小學的“奧數”題難倒了菲爾茨獎得主、俄羅斯數學家安德烈?奧昆科夫。但奧昆科夫絲毫不以為意:“做太難的題目會傷害孩子們學習數學的興趣。”其實,數學家明白的道理,中國的家長們也明白。但在數以億計的奧數經濟和升學壓力的驅動下,很少有人愿意傾聽那些被迫學奧數的小學生的聲音,結果是“奧數”班大行其道,揠苗助長、荼毒天真。
幾年前,我曾經質問過女兒的老師,為什么給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出那么難的數學題?“水池子一個口子出水,兩個口子進水,而且水流速度各不相同,問什么時候可以把水池子灌滿。”為什么不把出水的口子堵上再注水?老師的回答不緊不慢:“生活是復雜的,銀行的儲蓄所就是同時有人存款,有人取款。”我一時語塞,但仍滿心狐疑,小學生需要學習管理銀行嗎?
不過,“生活是復雜的”,老師的這句話倒是沒錯。現實生活中,出于自身利益,強迫別人做自己不愿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事的例子比比皆是。
多哈回合自去年7月再陷僵局,原因是美國的利益集團經過計算,認為目前的談判成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但怎么才能讓別的國家,特別是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再額外做一些減讓呢?按照現在放在桌上的文件,各國應該按照議定的公式削減關稅,同時發展中國家享有一定的靈活性,對一定比例的產品可以作為例外自主地處理。經過7年的談判,對公式的系數、靈活性的比例、待遇等問題都已大致達成共識,并且是互為條件的。如果明言全部推倒重來,顯然會招致反對,也與自身利益不符。于是,他們盯上了本來文件中一個不起眼的補充性的規定,即在達成“核心模式”后,成員之間可以對一些部門在自愿原則基礎上進行出價、要價的談判。然而,美國通過人最近拋出的“越過模式”的新建議早已把“自愿性原則”拋到九霄云外了,目的只有一個――把發展中國家本該享受的靈活性壓榨殆盡。本來可有可無、兩廂情愿的事,卻喧賓奪主、本末倒置,變成強制性的義務和負擔,變成多哈版的“奧數”。
成長中的孩童需要學習新知識、完成必要的學業,同時他們有休息、娛樂和自由選擇的權利;發展中的國家需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并承擔和自身發展水平相應的義務,同時他們有權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間,以便對本國經濟進行調整,包括對弱勢產業提供必要的保護以緩沖國際競爭的壓力。
回到開始的那道題吧。可以有兩種解法:
數學題范文第3篇
時間就是那么的匆匆,并且沒有痕跡,六年的小學時光就在彈指一揮間所剩無幾了,六年里的小學生活里,我感覺自己都被友愛包圍著,同學之間的友愛就在一聲問候中,一個微笑里,一個眼神里……
說到同學間的友愛,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四年級的時候,當時我的數學成績并不好,每一次考試成績都很差,甚至有一次考了不及格,這使得我開始不喜歡數學這門學科,上課時也開始不認真的聽講了,作業更是做得一塌糊涂, 打開我的數學作業本,放眼望去基本上全是叉,老師也曾在課堂是批評過我,可是我卻并沒有認真對待,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我在學校寫作業時遇到了一些難題,我習慣性的準備放棄,空著不寫的時候,我同桌拍了拍我,說:“你這些題都不會嗎?來,我教你吧。”我先是愣了一下,趕緊掩飾自己的心虛,使勁搖搖手說:“不用......”可我話還沒說完,她搶過我的本子講起題目來,剛開始我還有點敷衍,心想,老師教的我都沒聽懂,你教還不是一樣?不過因為同學的好意,我還是接受了,心猿意馬的聽著她的講解。可是,沒想到在一次考試時,就因為我上次聽了我同桌講的一些解題思路,發現不少原先不會的題目忽然會了,考卷也好像變的容易了,那次考試我的成績有一些提升,這一下讓我嘗到了學數學的甜頭,從那以后,上課認真聽了,作業認真做了,同桌也發現了我的改變,笑著說:“怎么樣?數學不難吧?”我不好意思的點點頭,又感激的說:“謝謝你上次教我的解題思路。”她卻毫不在意:“那沒什么,同學間互相幫助是應該的,下次有不會的我們再一起討論。”當時我的心里滿是感激。從那以后只要有不會的題目,我都會主動問同桌,她也幫助我解決了許多難題,并把她的學習方法分享給我,在我數學成績提升的同時,我也感受到了同學間最真摯的友愛。
同學間的友愛可能只是體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你借我一支鋼筆,我借你一塊橡皮,可正因為這些小事卻成為了同學之間的一種友愛的羈絆,大家彼此相互微笑著,勉勵著,努力著,成長著……
數學題范文第4篇
“這種題型明明重點講過、練過,學生為什么還是不會?”學校里經常聽到這樣的話。作為教師,我也常有同感。最近我們二年級進行了一個單元測試,其中一道操作題的答題情況,再次勾起了我的這個困惑。該題是讓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小魚向左平移10格后得到的圖形。”“在方格紙上畫出平移后的圖形”是人教版二年級下冊《平移與旋轉》這課的教學重難點,為了突破此難點,我頗費心思,制作了多媒體課件,通過直觀形象的動態畫面演示,讓學生了解什么樣的現象是平移與旋轉,如何畫平移后的圖形,即“先平移點,再連點成圖”。課堂上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多次練習“畫平移后的圖形”,每次做到及時反饋,面批面改。按常理推測,此題學生應當不成問題,正確率應當不低于80%,可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正確率只有 51%。與預期結果相差如此之大!明明都已經重點講過,還不會,為什么?
通過對學生的調查,我發現學生之所以做不出來,除了粗心、隨意等慣常原因外,主要原因是學生在平移點的過程中把起點數作“1”。第一次練習中我就發現這種情況,當時便在課堂上講解了,為什么還有這么多學生犯同樣的錯誤,我的課堂教學問題出在哪?我反思自己的教學并查找資料,特級教師徐斌執教的《平移與旋轉》對我啟發很大。以下是徐斌老師在講授本課時的教學片段:
師:下面跟著老師一起去草地上看看吧。看,來了三只小兔子。原來它們正忙著搬家呢。(出示簡化的格子圖)
師:瞧,小房子的運動方式是什么?
生:它是平移的。
師:它是向哪邊平移的呢?
生:它是向右邊平移的。
師:再看一看小房子是怎樣平移的。(再動態演示一次平移的過程。)
師:小兔子們覺得有些累,就停下來休息。
(課件分別出示3段錄音:第一只小兔子說:“你們看,我們的房子向右平移了3格。”第二只小兔子說:“不對,應該是向右平移了5格。”第三只小兔子說:“你們說得都不對,我們的房子是向右平移了7格。”)
師:同學們,你們同意哪種說法呢?在小組里相互說說。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然后匯報各自的想法。但是沒有統一答案,大家爭論不休。)
師:既然我們都不能確定到底向右平移了幾格,那么就一起動手來操作,通過自己的實踐來證明到底哪一種說法是對的,好嗎?
生:好。
師:請同學們拿出練習紙(小房子平移圖已經畫好),在左邊的小房子圖上找一個你最喜歡的點,再到右邊的小房子圖上指出它平移后的位置,并數一數,然后說一說你喜歡的“點”向右平移了幾格。
師:(幾分鐘后)你選的是哪個點?平移后的位置在哪里?平移了幾格?
生:我最喜歡的點就是屋頂了,我數了一下,屋頂從左向右平移了7格。(教師同時在實物投影儀上演示)
師:大家看懂了嗎?你們同意嗎? (一些學生點頭表示同意)
師:還有誰和他選的不一樣?
(教師指名三到四名學生匯報,并注意抓學生回答中的閃光點 加以鼓勵,然后同桌交流。)
師:你們找的點向右平移了幾格?都是7格嗎?
師:我們再來看看,小房子到底向右平移了幾格。
(小房子整體動態平移演示:一格一格地動,動一格停一下,讓學生數一次。)
師:結合剛才的操作,你們發現了什么?
生:我找了兩個點,一個點是屋頂,一個點是屋檐,發現它們都是向右平移了7格。
(教師結合學生的回答總結:不管哪個點,都是向右平移了7 格,正好和小房子平移的距離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以后數一個圖形平移了幾格,只要在這個圖形上找到一個點,看這個點平移了幾格,它所在的圖形就平移了幾格。)
結合徐老師的教學,反思自己的課堂,我基本上知道自己的問題出現在哪了。
為什么學生總是把起點數作“1”呢?受數數方法從“1”數起的負遷移是原因之一,根本原因還是學生沒有真正理解平移的本質,多媒體動態畫面演示,雖然直觀形象,但沒有學生真正的自主參與,沒有學生真正的探(下轉第81頁)(上接第22頁)索與發現,他們只是在模仿。難怪有的學生課堂練習時模仿對了,過幾天再做又錯了。徐老師精心預設了一個“小兔子搬家”的情境,特意出示三只小兔子對小房子平移幾格的爭論話語,讓學生加入到這場爭論中。學生的探究欲望被激發了,再引導學生分兩個階段進行探究性學習:一是觀察畫面,選擇自己喜歡的某一點,看看移到哪兒了,再數一數移動的距離(幾格);二是選擇其他點進行嘗試,然后討論與歸納,得出多個點情況是一致的結論。
數學題范文第5篇
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到小小的數學題讓我體會到了如山般嚴肅的父愛。
記得那是一個寧靜的夜晚,在明亮的燈光下,我正奮筆疾書,突然一道我沒見過的數學題如同一堵厚實的墻,擋住了我的“去路”,我急得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我想快點沖破這道阻礙,但是又無可奈何。頭上的汗珠一滴滴滾落下來,我如坐針氈,絞盡腦汁的去想,可這道“墻”好像就是跟我對著干似的,就是不讓我過去。百般無奈,我只好跑去問爸爸。我輕輕打開父親的房門,問道:“爸,這道題怎么做,教教我吧。”“自己想去。”正在埋頭看書的爸爸頭也不抬。我愣住了,像被冷水澆了一樣,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哼,誰要你教,我自己也做的出來!”我把房門“砰”的一關,用慍怒的眼光看著那道可惡的數學題……沉思片刻,腦袋里好像出現了兩個小人在爭論。其中,一個人說:“父親之所以這么說,是想讓你獨立思考,不依賴別人。這樣你才能真正懂得那道題的解法。”想到此,我的心豁然開朗。我冷靜下來,不一會兒,這道難題就被我“攻克”了。當我興高采烈地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父親時,父親笑了,笑得是那樣燦爛……
一道對常人來說微不足道的數學題,讓我懂得了那如山般深沉而又嚴肅的——父愛。
指導老師:曹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