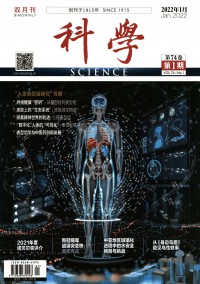科學哲學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科學哲學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科學哲學范文第1篇
【正文】
邏輯經驗主義瓦解之后,科學哲學領域出現了繁榮氣象,哲學家們從科學史、社會學、心理學、解釋學等諸方面對科學知識的性質、科學知識的形成、科學理論的發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種學派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如大江風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爾(DavidBloor)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圍繞這個強綱領形成了愛丁堡學派。布洛爾的《知識和社會造型》[①]對科學知識作了社會學的考察,提出了關于科學知識的新問題和新見解。多數科學哲學家致力于科學合理性規范,并把這個任務看成哲學的特殊任務。他們力圖通過闡明真理、實在等概念來說明科學的合理性。他們認為,知識是信念之事物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與證據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系統內部的一種關系。這種科學哲學觀基本上為科學社會學家所接受。許多社會學家認為,知識的性質(真假)不受外部的社會環境的制約,知識社會學不能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
在《知識與社會造型》中,布洛爾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他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驗本質,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等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將被完全作為社會學研究的資料來處理。布洛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得出的兩個重要結論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級的或先驗合理性、客觀性、有效性標準,以建立和提供這些標準為核心的哲學是科學的累贅,多數時候對于科學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制度的產物。
強綱領的主要立場是,在說明為什么某人或某群體持有某個具體信念、為什么某一信念發生轉變這個過程中,那些信念是真還是假、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等考慮是無關緊要的。布洛爾的強綱領有四個信條:(1)因果性對信念和信念變化的說明是因果說明,這要求我們考慮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會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對等性我們常常拿合理與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敗來評價我們的信念或知識,科學社會學必然對它們作出對等的說明。(3)對稱性科學社會學的說明必須是對稱的,比如說,同一種原因是既能說明真信念,又能說明假信念。(4)自反性科學社會學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說明模式必須適用于它自己。否則,科學社會學將是對自己的反駁。布洛爾比較接近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種自然現象,他的計劃對信念作出因果說明,就象物理學說明運動現象一樣。但是,他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結論卻在哲學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導致工具合理性逐漸取代規范的合理性。與實證主義的、歷史主義的、波普主義的、實在論的科學哲學不同,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關心對科學家的活動作經驗解釋,而不屑于科學合理性的規范解釋。他們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試圖把哲學家喜愛的規范擱在一邊而又能對科學作出說明,這個領域現在叫做“科學和技術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STS)。一般認為,STS在學術上是圍繞著社會學進行的,但不可能脫離哲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初的愛丁堡學派就是如此。在布洛爾的影響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與普通的科學社會學不同,STS學者以分析的分離和認識的中立精神來研究科學。這就是說,他們盡可能使他們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關于STS應采取什么態度對待科學,成了爭論的焦點。
STS使那些關心科學合理性和實在論的哲學家很不滿意,因此受到許多批評。但是,這個領域取得了許多的成功,這就迫使哲學家們考慮:如果不提供關于科學合理性的規范說明,會受到什么重大的損失?現在回答“損失不多”的科學哲學家越來越多了。吉厄(R.Giere)是這個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爾的論證,同時又承認,布洛爾的哲學敵手沒能證明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之外有一個單獨的“科學合理性”領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詞來說明科學中的認識的成功,這個概念也是布洛爾的知識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這樣,吉厄和布洛爾就聯起手來了。吉厄說,不論過去是一些什么樣的策略產生了認識論上可向往的結果,這些策略應該在將來配用到相似的場合中,這樣就隱蔽地承認了這些關于研究目標的策略在具體場境中的相對性。布洛爾的強綱領的追隨者巴恩斯(BarryBarnes)則使用了一個更有刺激性的詞,即“自然合理性”[③],它與“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還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學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過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爾的強綱領導致科學哲學的方向發生變化。哲學以什么方式來解釋科學,現在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傳統的科學哲學認為,理解科學的最適當的手段是對科學理論作邏輯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庫恩這樣的反傳統的哲學家也大致上是這樣解釋科學的。自然,多數哲學家不愿意改變這種解釋科學的方式。他們力圖說明科學哲學與STS有實質的區別。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并不否認這種區別,卻認為與STS有區別的科學哲學并無存在的理由。
蒯因是“認識論自然化”的開拓者。一般認為,自然主義在心理學上持還原論立場。例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紅色。”這里涉及一個認識概念,即“信念”。信念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并不是一個實在的事件,我們可把它還原為一種經驗的相互關系,即神經狀態(事件、過程)和具體的環境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信念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現代認識論和心理物理學站在一邊,而知識社會學卻站在對立的另一邊。按照現代認識論和物理心理學的圖畫,孤獨的有機體與它的環境(包括其他類似的有機體)相互作用。但是,知識社會學家懷疑這幅圖。這種沖突在心理學中也有表現。例如,弗多爾(JerryFodor)和吉布森(J.J.Gibson)之間有一場關于“唯我論的”和“生態學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相對優點的爭論。弗多爾論證說,專注于孤獨的認識者具有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論力量,因為它使心理學家達到思想的規律,本質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對象,因此,心理學承認“方法論的唯我論”[④]。
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識社會學的建立者,以他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爾。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不同于科學哲學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認識論。為了了解這種區別,考慮人們提出的有哲學意義的“知識問題”的兩種策略。
策略A:(1)我最了解我的心靈,但它可能不存在。(2)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們存在,由于它們似乎與我自己的心靈不同,我如何認識它們?
策略B:(1)我們日常感覺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當我們編排(articulate)他們的經驗時,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夠直接到達的世界的外觀中有著顯著的差異。(2)那么是什么使我們達到我們共同的實在有這些差異呢?是什么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忽視這些差異、認為我們自己達到的與所有的人都一樣呢?
羅蒂、笛卡爾、蒯因等采取了策略A,由內到外提出知識問題。而知識社會學則采取了策略B,由外到內說明知識。布洛爾也采取策略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布是一個認識論的實在論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數人也是實在論者,因此他不相信預設實在論有助于說明各人信念的差異。有些哲學家擔心,知識社會學的“相對主義”意味著反實在論、懷疑論、虛無主義或更壞的東西。針對這些哲學家,巴恩斯和布洛爾說,“總的結論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認識反應中,實在畢竟是一個共同的因素。作為一個共同因素,用它來說明那些差異,沒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對主義提出來,是作為某些可能與實在論相伴隨的不良認識習慣的補充,特別是當一階“自然態度”的實在論被捏造成二階的普遍研究原則的時候[⑥]。這些不良習慣有兩個傾向比較突出:(1)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信念的差異;(2)別人與我們的信念有差異,如果這種差異不能完全解釋透,就夸大這些人的病態。在強綱領的四個著名信條中,布洛布表達了他認可的相對主義。這四個信條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這幾點被稱作“信條”,批判者把它們當作無條件的認識論原則,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啟發法,研究異族文化知識的研究者一般都會有這樣的偏向。
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一旦自然化會怎樣呢?可以預料,布洛爾會同我們更一般的自然主義者分手。布洛爾和曼海姆對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計,而這估計是布洛爾在科學哲學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種:(1)哲學增加它相對于具體科學的優越性和獨特性;(2)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獨特性;(3)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越性,也失去其獨特性。
前景(1)很難受到贊賞,甚至很少討論,因為這意味著自然化的哲學將會同科學作對。然而,假定自然主義者試圖在認識上推進科學,那么這種動機有什么根據呢?在通俗的和社會學的文獻中充滿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現在是誰站在爭端之上俯視相競爭的領域的相對優點?理想地說,是一個對于各門具體專業的進展沒有利害關系的人,這個人能是一個哲學家嗎?也許,如果哲學失去特有的題材,如果沒有特有的題材不被看作弱點,而被看作優點:在對立的學科之間作調停,那么俯視具體爭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學家了。哲學家對這樣的結論并不感懷,這是因為它要求設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學科標準的研究評價標準,這種事情現在哲學家越來越不愿作了。現在比較前景(2)和(3),布洛爾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1985)、吉厄(Giere1989)、福勒(Fuller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關于自然化認識論者或科學哲學家的職責,反復出現的比喻是“知識工程師”、“科學政策家”(sciencepolicymaker)。這兩個比喻都保留了哲學工作的規范特性,但沒有傳統哲學對立法的那種無限制、無條件的態度。簡單地說,自然化的認識論是應用科學的一個分支,它只假說式的、而不是關于研究行動的絕對命令。因此哲學對于具體科學仍然是獨特的(如果不是優越的),這是前景(2)。按這個前景,哲學不優于(可能劣于)當前最好的科學。
現在轉向前景(3)。A和B兩種策略對它的解釋有實質性的差異。羅蒂和屈奇蘭(P.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們的自然化的認識論主張取消關于認識的哲學理論,代之以心理-物理學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哲學特有的東西”留下來,因為哲學只不過是原始的科學罷了。布洛爾也同意開除哲學——它既不是科學,也沒有獨特的題材。但是,布洛爾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羅蒂和屈奇蘭為哲學家描繪出的畫像是:哲學至多只是合法的問題,但用不恰當的手段回答它們,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爾看到的則是哲學家最大的特點:哲學只不過是加強了那些來自自然實在論的不良習慣。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說起來多么有理,其實是鼓勵他們的自然傾向,似乎認為對他們最清楚的東西(makemostsense)應該對于每一個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爾并不認為合理性理論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有某種必然的邏輯聯系。他得出上述結論,是根據一個經驗論題:以這樣的合理性理論裝備的研究者與無此裝備的研究者相比,更少有可能得到經驗上恰當的理解知識如何運轉。但是,“經驗上恰當的理解”這個概念是否預設另一種特別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論呢?可以設想,布洛爾和多數STS學究一樣持約定論的態度,把答案推給某些行動,在一個相關的尋求知識的共同體(它提供知識社會學的模型)中,這些行動顯示了“經驗上恰當的理解”。布洛爾的強綱領是打破了傳統哲學的自我形象。可以說,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爾的自然主義的特點。(1)哲學引導我們選取科學作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們發展真理、合理性理論,這種理論迫使我們用嚴格的邏輯推理標準來辯護我們的知識,這又進一步揭示了我們自以為是(takeforgranted)的思想習慣的不恰當性。(2)但是,一旦我們開始作科學,我們發現這些哲學理論是進一步研究的障礙,因為它們鼓勵我們以很少幾處知識片斷為根據,急急忙忙得到關于整體的結論。這個走向不成熟的總體化的傾向產生于我們試圖讓理性做經驗觀察所做的事。(3)這說明,這種思想方式是要說服我們相信科學的價值,一旦我們被說服之后,這種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對科學有所補益。事實上,這種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個障礙,應該被擱置,因為它的用處已經用過了。
維特根斯坦把哲學比作梯子,一旦用過之后就要丟棄了。布洛爾的“反哲學”態度大都來自維特根斯坦,社會學家孔德、曼海姆也對布洛爾有一點影響。
布洛爾提出以自然主義方式取消哲學這門學科,這使哲學家們最為惱火。羅蒂和屈奇蘭認為哲學是認識實踐的先鋒(precursor),多數哲學家,至少認識論者和科學哲學家,認為這是正面的文化貢獻。而布洛爾認為,在科學占主導地位的認識文化中,哲學是一種返祖現象(atavism)。在哲學家與科學家的關系上,雖然有的哲學家(波普)要求科學家更像哲學家,有的(屈奇蘭)要求哲學家更像科學家,但哲學家一致認為他們自己最終是站在同科學家一邊的。布洛爾否認這一點,認為只有在科學不是占主導地位的認識實踐的文化中,哲學才是站在科學家一邊的。
波普認為哲學家使科學家保持警覺,周期性地(反復地)把他們從教條的、常規科學的沉睡中喚醒。而布洛爾認為,哲學使科學浸染上一些習慣,這些習慣使科學難以持久,時間一長就做不了。例如,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通過不斷地進行推理,伽利略揭示了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假定的人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一個更好的物理學家是不會僅僅通過使用這些力量得來的,因為這只會導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成為“第一原理”,如同笛卡爾的物理學。布洛爾斷定,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經驗上的第一原理,如牛頓所說的,“從現象出發作推導”。科學最后總是要擺脫哲學的。這個說法顯然認定科學與哲學只在某些場境中是相互相容的,而另一些場境中則互不相容。科學與哲學有時形成暫時聯盟反對共同的敵人,如亞里士多德或基督教,但一旦這個敵人被戰勝,科學占了支配地位,科學的科學(例如強綱領)就會花很多時間清除科學中的哲學殘余。布洛爾就是這樣看他自己的計劃的。
在敘述普利斯特利接近發現氧時,布洛爾試圖把真理概念中的麥粒與麥殼分離開來,這個真理概念是說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沒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爾,“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觀念真,某某觀念假”等說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即把我們與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觀念(“真”觀念)和我們不與他共有的觀念(“假”觀念)區分開來。然而,布洛爾認為,如果我們輸入一種更“哲學的”真理觀念:我們稱為“真理”的那組觀念比我們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實在——獨立于我們求知的利益(interests),那么我們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這種哲學的“累贅”(encumbrance)包裝進真理觀念之中,我們于是就能剝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用我們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然后用適合于推進我們自己的利益的標準來判斷他的工作。關于那些標準是什么,我們處在完全同意的狀態之中,我們幾乎不需要討論它們,因此它們對于我們不表現為利益。布洛爾從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啟發,把這種由現在的利益(concern)系統地代替過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論”的合理性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常常被混同于關于理性如何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釋。
通觀《知識和社會造型》,布洛爾用來刻畫關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學”觀念的詞匯如“意識形態”、“分裂”(divisive)、“高壓”。“高壓”一詞來自杜克海姆(Durkheim),杜克海姆認為,一個真理就是一個信念,共同體根據這個信念迫使它的成員以某種方式行動。不論哪種情況,哲學研究都是科學研究的包袱(im-pediment)。實際上,布洛爾試圖作一個更強的論斷,這一論斷在第四章(關于波普-庫恩之爭)講得最清楚:哲學把科學不必要地政治化(philosophypoliticizesscienceunnecessarily)。“我想提出的論斷是:除非我們對于知識的性質采取一種科學態度,那么我們對這種性質的掌握不過是我們的意識形態的關心(concern)的一個射影罷了。我們的知識理論將隨著相應的意識形態的興衰而沉浮,它們將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發展基礎。認識論將成為一種純粹的隱性宣傳。”[⑧]
現在,庫恩一般受到的指責是他用“革命”一詞夸大了概念變化的不連續性。有趣的是,布洛爾在更深的層次上指責庫恩求助于“革命”,指責他以不同的手段給哲學即政治學的傳統輸液。布洛爾認為,波普和庫恩為哲學家開了方便之門,使他們可以利用科學史,從中舉出大量的例子表達他們喜愛的體制(regime)。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有一個可檢驗的科學變化的經驗模型的形狀,但它那使人興奮的政治造型致使庫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對話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義,回到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世界。
布洛爾沒有樸素地相信科學能夠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學。強綱領的一個最著名的實質性論題是,一切科學都是受利益驅使的。然而,承認科學中持續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贊成這種利益的出現,因為有些利益可能腐蝕社會學家對科學的理解。這個方面,許多哲學家有意無意地誤解布洛爾。布洛爾攻擊哲學對科學的不良影響,他同后期維特根斯坦一樣,把哲學看做一種獨特的“生活形式”,認為科學家的實踐是一種以歷史為根據的自身整體(histor-icallybasedintegrityoftheirown)。當然,實踐科學家可以合法地改變科學實踐。科學家對更大的社會的或自身利益的關心常常是他們的研究活動的一個因素,但這個因素只有在它們實際上改進科學實踐的時候才有益于科學實踐。誰決定實踐受到了幫助還是受到了損害?這是一個經驗問題,是由一個具體共同體的科學家來解決,社會學家處在發現其結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學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對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驗意義,而多數實踐科學家又沒有認識到,那么哲學可能模糊社會學家和實踐科學家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喪失了他們代表科學的力量,政治學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勝利應該受到指責。
可以說,布洛布是一個自然化的認識論者,他還是一個特別自身一致的自然主義者:宣布他已經以科學的方式確定了他自己的領域-哲學-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注釋:
[①]D.Bloor,KnowledgeandSocialImagery,1976,1991,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②]R.Giere,ExplainingScience,ChicageUniversityPress,1988.
[③]BarryBarnes,"NaturalRationality:AneglectedconceptintheSocialSciences",Phi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76,6.
[④]JerryFodor,"MethodologicalSolipsismConsideredAsaResearchStrategyincognitivePsychology,inRepresentations,MITPress,1981.
[⑤]B.Barnes,andD.Bloor,(1982),"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gyofKnowledge",inM.HollisandS.Lukes(ed.)RationalityandRelativism,MITPress.P.34.
[⑥]A.Fine,UnnaturalAttitudes:RealistandInstrumentalistAttachmenttoScience,1986,95.
[⑦]W.V.O.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H.Kornblith(ed.)NaturalizingEpistemology,MITPress,1985.
R.Giere,ScientificRationalityasInstrumentalRationality,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1989,20.
科學哲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生有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要比自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科學哲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
【正文】
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碩果。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顯然是不夠的。科學也是一種社會系統或社會體制,并且科學知識本身同社會條件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還需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元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難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起步較晚,加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誘人的應用前景,使得科學社會學研究正方興未艾。尤其是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大有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社會學的趨勢。本文對元科學研究的這一發展趨向作了評析,認為:(1 )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難以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2)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科學哲學的這種局限性, 從而促進其深入發展,而且也為整個元科學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3)科學社會學(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學哲學對科學內容本身作深層的研究。
一、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盡管關于什么是科學哲學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一般說來,人們基本上還是傾向于將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下面的一門二級學科。更確切地說,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 科學哲學主要探索下列問題:(1)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2 )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3)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 (4)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學哲學要比科學本身的實踐站得更高:科學從事的是對事實進行解釋,而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p.2)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洛西將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將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看作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約翰·洛西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似乎科學存在著一種超歷史的結構或方法論規則,而科學哲學可以站在科學之上,運用超歷史的元科學概念,揭示科學的程序、結構或科學解釋的邏輯。二是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他們將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從而將邏輯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考慮則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純粹局限在認識論范圍內研究科學,完全忽視了社會學的因素,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
應當肯定,傳統的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分析,關于科學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對若干元科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等等,對于推進和深化科學認識論乃至整個哲學的研究,無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由于他們對于分析、還原和邏輯方法的強調和運用,使得科學哲學幾乎成了一門與科學研究相類似的相當嚴格和精密的學科。他們發起的“科學的哲學”運動盡管后來遭到失敗,但的確曾經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輝煌的時期,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哲學的發展。因此,從歷史的觀點看,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此定位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是對于推進哲學還是科學研究來說,也許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頗性;首先,雖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是它本身卻應當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它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若是按照傳統的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和認識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這種角度嚴重地忽視了科學在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一重要特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往往并非單獨地從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研究;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公共)性的事業,其中個人的行為要受到社會目標和規范的強烈影響;還有任何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往往不能脫離社會對技術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和偏頗性,將認識因素和社會因素密切地聯系起來,更進一步說,如何將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有機地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應當說,托馬斯·庫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庫恩提出的兩個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可以說既是科學哲學又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解釋科學的動態過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究竟是怎樣發展的。在他看來,這種“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就是說,必須描述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必須分析傳遞和加強這個體系的體制。知道科學家重視什么,我們才有希望了解他們將承擔些什么問題,在發生沖突的特殊條件下又將選擇什么理論。”([2],p.286)由此可見,盡管庫恩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帶有嚴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庫恩對于糾正傳統的科學哲學片面強調“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溝通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和科學心理學的聯系,開辟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貢獻是巨大的。
自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理論以后,科學哲學逐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歷史主義者們大大超越了傳統的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更多地關注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他們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即歷史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主義者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
然而,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一種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仍然沒有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邏輯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也就是說,歷史主義者最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于是,科學哲學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關于科學進步的問題。本來,如果真正從這社會歷史的觀點看,科學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首先,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先進的物質手段從事科學;其次,人們可利用的知識和信息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增長;還有,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和發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在分析哲學的框架內,用純粹邏輯的觀點來解決,科學進步問題卻變得極為艱難。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科學哲學家們至今還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兩難困境:要么堅持某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學進步標準來說明科學的進步性;要么接受庫恩的觀點即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由此可見,要使科學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應當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進一步開拓視野,積極吸取其他元科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使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科學社會學的新視野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它們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哲學主要地將科學看作是一種認識,往往使用認識論的范疇(如“理論”、“因果性”、“實驗”、“假說”等等),對科學側重于進行方法論或認識論以及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研究。然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在本質上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將科學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科學在社會中逐漸體制化的過程。于是,科學社會學往往使用社會學的范疇(如“體制”、“規范”、“分層”、“權威”等等),對科學重點進行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具體地說,科學社會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一,與其他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樣,科學也是一種社會體制。“科學可以被樸素地表達成由許多科學家個人組成的共同體:他們觀察自然界,互相討論他們的發現并且把結果記錄在檔案中”,“在可能達到的最廣泛的范圍里,致力于建立觀點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正常運行是通過許多公共的或社會的形式來實現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里的科系、學術社團及科學雜志,它們致力于各種各樣的公共活動,象科學教育,發表科學論文,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展開辯論,或者對于著名的發現授予正式的獎賞。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們注意到了公共性影響,如教育課程的設置、研究傳統及研究綱領。每一個科學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種各樣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員或知名科學權威,并且受到公共行為規范的制約,如‘普遍性’或‘無私利性’等。”([3],p.13 )科學社會學(至少是“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將這些公共建制、活動、影響、角色、規范等等看作是“科學的基本要素”,強調“如果不去探求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彼此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那么就無法理解科學理論的地位,無法理解這些理論當初是怎樣被設想出來的。”([3],p.13 )這就是所謂“內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和出發點。概括地講,“內部的”科學社會學,按照齊曼的觀點,是以科學發現為背景,研究的是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
顯然,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的研究綱領大大拓展了元科學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研究。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已經觸及到用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僅僅是綱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學哲學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難能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歷史案例中去尋找科學發展的邏輯。相比之下,科學社會學不僅使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切切實實地推進了這方面研究。例如,科學哲學中提到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等等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那里已經不再是一種智力抽象,而轉變成為切實的研究對象。至于科學哲學中非常突出的“客觀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問題,科學社會學則用社會學的術語重新加以闡述。約翰·齊曼甚至提出了“社會學的認識論”的概念。在他看來,“社會學的觀點不僅闡明了科學的‘方法’;它也說明了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3],p.159 )他指出, “代替強調科學的認識方面的哲學透視,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采取社會學的觀點。”([3],p.149 )這些話可能有些夸張,但是, 對科學內部作社會學的研究對于科學哲學來說至少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其次,開辟了許多關于元科學的新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例如,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關于無形學院的研究,關于科學交流體系的研究,關于科學獎勵制度的研究,關于科學家行為模式的研究,關于科學中的社會分層的研究,關于社會中的科學家的角色研究和關于科學評價的體制化研究等等,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于理解科學內部實際的社會運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更重要的是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探討,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對科學的控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后果等等。科學社會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相反,它更強調科學“這種社會建制植根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完成一定的社會功能,并且和其他體制一樣,和法律、宗教、政治權力等等聯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學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科學通過技術以巨大的力量導致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科學的發展既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不恰當的應用而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科學又受到社會的巨大影響、制約或控制。從經濟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技術上的需求,社會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方向;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從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無法脫離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受到這種文化環境的制約。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將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工具,使它服從于各種社會需要,而且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科學的體制及其自身的活動方式。當然,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制約或控制也會有雙重效應:一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壞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給科學與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毫無疑問,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對于元科學研究來說,帶有革命性的變化。它的意義在于:
首先,突破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史、甚至“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學本身的活動范圍內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那就是科學正在改變著整個社會,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改變著科學。用約翰·齊曼的話來說,“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使科學自身內部的活動方式變得面目全非,并且這種力量正在向著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的核心滲透:而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這種情況。”([3],p.11 )也就是說,如果切斷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系,即將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忽略不計,而單純地研究科學本身,則多少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只是從“內部”研究科學,其視野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學術活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為科學而科學”。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的確,科學是一種條理化的知識體系;它采用了獨特的方法;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們做出的發現。然而,它更是一種與整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體制;它是一種實現各種社會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質設備;它是教育的主題;它是文化的資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類事務中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科學‘模型’,必須把這些相互差異、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聯系起來,并且統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將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聯系起來加以綜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開辟了元科學研究從理論走向現實的更廣闊的道路。由于對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忽視,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它們所建立的各種科學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學作為學術活動的模型,離科學作為社會體制的現實情況有很大距離。相比之下,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更著重于關注科學的社會現實:究竟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通過技術影響社會的?社會又是如何實際地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科學在現實社會中的現狀是什么?它將如何發展?科學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負面影響?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既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它所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可以說,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為著重運作的關于科學技術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否取代科學哲學
很明顯,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科學社會學同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來研究的科學哲學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而且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學社會學大為不同,它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不是從社會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而是強調要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因素的關系。這便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兩者之間的互相競爭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蘊含著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夠而且應當取代科學哲學,來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項“強綱領”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或超驗的特性,也不存在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這樣的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應當徹底地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材料來處理。([5],p.3)這無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學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為內容的科學哲學應當終結,關于科學知識的一切應當讓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研究。我們認為,這種見解不僅是相當偏頗的,而且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個側面,它根本無法代替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本身作正面的認識論的研究。我們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維·布盧爾在他的《知識和社會建構》一書中對“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闡述。布盧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純粹是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看待的。”([5],p.5)他認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循以下四條原則:①知識社會學是研究原因的,即關注那些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其它類型的原因,它們與社會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識社會學公平同等地對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都需要得到解釋;③知識社會學的解釋風格是對稱的。例如,用同樣類型的原因來解釋正確的信念和不正確的信念;④知識社會學是反身性的,從原則上說,它的解釋模式應當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否則社會學將是對它自己的理論的反駁。布盧爾將原因、公平、對稱和反身性這四條原則稱之為是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定義。([5],p.7 )由此可見, 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科學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產生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它甚至根本不關心科學知識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這樣一些對科學知識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立場,將所有科學知識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為“結果”;它將研究重點放到了科學知識的外部,放在社會條件或原因上面,即側重于研究是什么樣的外部的社會條件或原因導致什么樣的科學知識的產生。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科學知識不能說沒有新意,也許是頗有意義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角度僅僅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科學知識,而且過多地強調這個側面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其一,正如約翰·齊曼所批評指出的,“固執的社會學家可能大大地過高估計了社會利益的影響和其它科學以外的考慮”,從而“鼓勵從在科學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發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結論”;([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學知識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等認識因素,而事實上這也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毫無疑問,離開了人的認識,社會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學知識也無從產生。
其次,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局限性。勞丹認為,“任何認識社會學的解釋至少必須給出存在于某個思想家Y 的某種信念X與Y的社會狀況Z之間的因果關系。 (如果社會學的解釋具有‘科學的’意義的話)這就要求助于一條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處于Z類狀況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數的)信仰者都會采取X類信念”。([6],p.217)但是,在勞丹看來,盡管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工作,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其解釋還是“過于粗糙,遠遠達不到起碼的確切性要求。” ([6],p.218 )除了象勞丹這樣的科學哲學家以外,還有象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對知識社會學最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之一卡爾·曼海姆都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前景表示懷疑。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內部科學史的范圍,并且大量地獨立于非純科學的因素。”( [6], p.220)而曼海姆則斷定說:“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6],p.220)一般說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困難及其局限性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特定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其二,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從宏觀上講比較說得通,而從微觀上分析比較困難。例如,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學科中,發展較快、成熟較早的是經典力學。但是,我們很難說明經典力學中的每一個定律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許比較適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經驗性很強的科學知識,但很難研究近現代那些理論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科學知識。因為前者離社會現實比較近,或許同社會條件有某種直接的關系;而后者離社會現實比較遠并且已經高度數學化。更進一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知識可以用理性解釋的范圍內似乎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內工作”,才有“廣闊的天地。 ” ([6], p.222 )當然,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范圍的限定未免有些絕對,但是,他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來代替科學哲學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顯然,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科學哲學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對科學知識的研究趨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將科學知識僅僅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他們不希望、也不可能對科學知識作比“自然現象”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將科學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問題擱置一邊的結果是,將科學知識等同于文學知識、道德知識、宗教知識或別的什么知識,使得科學知識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文化知識的特點。這樣一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在否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同時,實質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所作的研究,因為既然科學知識同其它別的文化知識沒有什么根本區別,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其二,進一步為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敞開大門。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學觀點。確切地講,他們認為,默頓學派的局限與不足就是與實證主義哲學的聯系,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學觀點的支配下,為科學社會學轉向科學知識內容的研究作出貢獻;并且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論證這些新的哲學觀點。 ([7],p.228 )而這些所謂的新的哲學觀點最主要的傾向之一,那就是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正如布盧爾所明確承認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依賴于一種相對主義。它采取了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早先提出的對稱性和反身性兩條原則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們得到如何評價)都將以同樣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釋。” ([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來論證哲學觀點,那么勢必強化相對主義的觀點:首先,科學哲學中所探討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其真實的含義只不過是“主體間性”,即“許多人的意見一致”。這就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觀點。其次,正如齊曼指出的,“知識社會學原則的嚴格應用看來必將導致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科學僅僅是在理智領域中許多相互競爭的世界圖像當中的一種,而且它并不優越于一個社會團體能夠贊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統方案,例如,贊德人的著名的巫術信念。”([4],pp.119—120)這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由此可見,如果說費耶阿本德從科學史的個別案例研究中得出認識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結論,從而宣告科學哲學的終結的話,那么,這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則試圖以更一般的經驗研究來強化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可是,他們竟沒有想到,科學哲學的終結同樣也意味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終結!
參考文獻
〔1〕 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馬斯·S·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 劉@①jùn@①jùn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John Ziman, Reliable Knowle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8.
〔5〕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Lmage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科學哲學范文第4篇
當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不僅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地影響著社會,而且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有力工具,前所未有的將人和現實、主體和客體緊密地聯系起來了。因而科學發展的動因、規律、發展模式與人類社會生活的種種關系理所當然地成了當代哲學所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
科學哲學是當代西文哲學中較晚產生的,有點獨特卻發展極為迅速,對自覺科學和社會科學都產生了極重要影響的一個新流派,現代科學哲學在20世紀20、30年展壯大以來,發展迅速,流派紛呈,主要產生了邏輯實證主義、批判理性主義、歷史主義等流派,他們圍繞著科學的劃界標準,對科學的發展模式、科學方法等問題進行了有效探索,并產生了各自的科學觀。
一、邏輯原子主義
邏輯原子主義是羅素把邏輯分析方法應用于解決本體論問題而提出的。羅素認為,存在世界是由許多事物組成的,但事物并不是構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事實,事實不是指某一事物,而是指某物具有某種性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
羅素的邏輯原子主義思想的形成同維特根斯坦有著密切的聯系。羅素在《邏輯原子主義》中指出:我稱自己的學說為邏輯原子主義的理由是因為我想在分析中取得的作為分析中的最終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質原子而是邏輯原子。
二、邏輯實證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其核心是維也納學派,也叫經驗主義,或稱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新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是傳統的經驗主義和邏輯分析方法相結合的產物,其思想淵源于休謨哲學、實證主義、馬赫主義和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實證主義是20世紀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石里克、艾耶爾、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問題是意義問題以及通過意義劃分科學和形而上學的界限。他們的綱領是:捍衛科學而拒絕形而上學。20世紀30年代末,隨著維也納學派的解體,作為一個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也就分化瓦解了,但該派所倡導的邏輯實證主義精神仍繼續存在。
三、批判理性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逐漸衰落,受其影響的一些學者對它的基本原則提出批判,從而形成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rationalism),后來研究者又將其稱為“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它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更為緊密,在50-60年代盛極一時,對哲學界和自然學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波普爾、拉卡托斯。
波普爾是科學哲學的創始人,他反對分析哲學認為科學只有在證實的基礎上才能成立的觀點,將亞里士多德“科學產生于驚訝”改成了“科學產生于問題”,論文經驗證實只是歸納的邏輯,而是歸納不可能提出必然,所以提出了經驗證偽原則,建立了科學發展“問題——猜測——檢驗——證偽”四個階段的科學發展的結構模式。
卡爾·波普爾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他提出了“科學發現的邏輯”,主張對理性應該采取批判的態度,認為普遍有效的科學理論并不來自經驗歸納,科學理論是通過不斷的證偽、否定、批判而向前發展的。
拉卡托斯是波普爾的學生,他批判地繼承了波普爾的哲學思想,提出了一種有獨到見解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斯反對庫恩所說的科學的范式轉換是新范式全部替代舊范式的一場革命,他認為新的科學研究綱領的確立應當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研究綱領的更新替換,另一種也可以是在舊的研究綱領的基礎上來一個包含了舊內容的轉換新生。
四、科學歷史主義
科學歷史主義脫胎于批判邏輯實證主義,經過批判理性主義演化而來,在60年代頗為流行。它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脫離科學發展的歷史,孤立地研究科學理論的方法,主張把科學看作是由許多相互聯系和依存的命題、定律、原理所組成的有機的系統整體,強調依據科學史和科學事實來尋求和揭示科學的內在結構和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該學派重視科學發展
轉貼于
的歷史,注重把科學理論與科學歷史聯系起來,并在這種聯系中探討科學理論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因而被稱為歷史主義學派,它比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前進了一步。
五、后現代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范文第5篇
關 鍵 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 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 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 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 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 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 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 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 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 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 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 、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 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 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 .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 )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 “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 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 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 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 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 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 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 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 ,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 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 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 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 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 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 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 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 ……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 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 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 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 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 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 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 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 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 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 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 生有 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 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 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 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 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 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 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 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 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 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 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 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 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 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 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 。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 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 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 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 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 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 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 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 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 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 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 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 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 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 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 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 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 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 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 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 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 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 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 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 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 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 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 [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 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 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 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 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 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 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 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 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 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 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 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 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 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 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 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 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 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 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 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 。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 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5]。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 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 。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 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 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 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От редак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J]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10):24-26.
[2]Стёпин В С, 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ов М 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EB/OL]. (2006-06-20)[2007 -08-02]. http:∥philosophy.ru/library/fnt/11.html.
[3]Розин В М, Горохов В Г, Алексеева ИЮ, et al.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 нность[EB/OL]. (2006-06-28)[2007-08-02]. http:∥philosophy.ru/ iphras/library/filtech.html.
[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